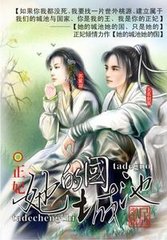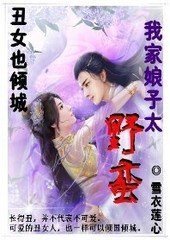荒芜城-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做过好多后悔不迭的事呢,又有什么关系。”她说,全没放在心上。
“他们说文身的位置不好,会倒霉。”我说。
“我每回文身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已经碰到最倒霉的事情,还能再糟到什么地方去呢。”微微说,“当然是会转运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分成有文身的人与没有文身的人,文了第一个以后就把自己归入另一类人里去了。”
所以之后当我俩站在一起的时候,也总是这样的。微微总是那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模样,她说话大声响亮,热气腾腾,随时都要拼命投入这个世界。而我则是她的反面,小心翼翼,羞涩不安,时刻提防世界的夹缝。在明明从未有过什么伤心事的时候,我的脸上已经布满担忧。
那么在当时,突然决定要去文身大概只是因为想要变成与微微一样的人,心情迫切到根本不在乎到底文什么样的图案,不在乎文在什么样的部位,所有的犹豫都变得微不足道,自己完全无法理解。
两三天以后,微微陪我去做了文身。我们在休息日的下午碰面,这是我第一次在咖啡馆之外的地方见她。那几日为了不碰到脚踝上的文身伤口,她都穿着短裤和拖鞋。我们的心里怀着些无以名状的兴奋,几乎算得上是雀跃。一路上她不断停下来,逗引一两只趴在屋檐上的野猫,欢呼着扑向一只过马路的流浪狗,与影碟摊上的小伙子打情骂俏,经过快要落市的菜场时,从门口的蔬菜摊上买了两根黄瓜,问鱼摊老板借水龙头冲洗干净,递了一根到我手上。咯嘣一口咬下去,清香四溅。她一刻不停地与我说话,一会儿走在我前面,一会儿走在我后面,一会儿与我紧紧地挨在一起。
我们都有一种面对新生活的新鲜感,对我来说尤其如此。
文身只花了半个小时,右侧脖子一株绿色的树苗。我趴在一张椅背上,上身脱得只剩下胸罩。空调开得太足了,我因为紧张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是文身师问我还好吧,我说没事,很好。然后他用酒精给我消毒,我还是缩了缩肩膀,倒不是害怕,稍微觉得有些孤独。与小时候打针前的感觉差不多。等到第一针下去,反倒放心起来。微微去隔壁帮我买了包烟,点好一根以后递给我,烟嘴被她咬得湿湿扁扁。
“疼么?”她俯身问我。
“还行。”我说。看着师傅不断用纸巾擦去从表皮毛细血管里渗出来的血,擦在纸上是粉红色的,刺痛感并没有我想像中的强烈,甚至感觉这是其他人的血。
“我第一次文身的时候,抽了足有大半包中南海,一根根的没有停过。痛不欲生的。一边骂人一边发誓说这是最后一个。”
“结果呢?”
“结果隔了两个月就做了其他图案,比第一次还疼,完了以后得立刻在隔壁吃碗热腾腾的米线才能长出力气来。半途还接到我妈的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家。她平时可不会这样问我,那天却说做了噩梦,梦见我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痛苦。她喊我的名字,喊不出声音来,在梦里急得哭起来。她做那个梦的时候,我正在文身台上躺着。”她说。
“她后来见过你的文身么?”
“隔了一段时间才见到的。差不多我做完第五个,别以为做五个花了很长时间,也不过是一年。那时候为了感情的事情难过得死去活来的,就搬回爸妈家里住了段时间。我妈妈年轻时是个飞妹,抽烟。现在也偷偷瞒着我爸抽。那回她偷听我躲在厕所里打电话,声嘶力竭地哭、哀求。等我挂上电话,她就递给我一根烟。”她说到这儿笑起来,“你别看我现在五毒俱全的,那是我抽的第一根烟。出于一种回报的心态,我就给她看了全部的文身。”
文身师是个不苟言笑的敦实男人,听到这儿他都笑起来。
“她说了什么?”
“跟你一样,问我说,疼不疼。”她说,“然后她认真地看了我的每个文身,详细地问我那些图案是什么意思。我的左后腰文了句英文,她问是不是我爱你的意思。说完我们都乐了。我说不是的,是‘挺住意味着一切’的意思。她看起来像是挺崇拜我的,然后她说没把男孩的名字文上去她就放心了。”
但其实那天我就知道,疼这回事情,不过如此。不过是两三根烟的工夫,图案就做好了。文身师拿了两面镜子给我,好让我看到树苗的样子。它瘦瘦弱弱,比我想像的要更小一些,沿着我左边那边薄薄的肩胛骨向上生长。有十来片叶子,下面伸出些细小的根须。它的位置有些太靠近肩膀,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衣服遮住。可是我心里其实对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所以也根本不会觉得失望。文身师叮嘱我这些天不要喝酒,不要吃辣,再买些金霉素眼药膏涂涂伤口。然后他转而对微微说:“你是久经沙场了,照顾她没问题吧。”
我们一起从店里走出来,外面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变化,西落的太阳恹恹地照在我们身上。在经过一间杂货店时我们停下来,要了两瓶可乐,站在那儿吮着吸管一气喝完。
“你为什么要文棵树苗?”她问我。
“担心自己总是离地太远,希望以后树根会真的长起来。”我说。
“它们才不会真的改变你。”她说,又点起一根烟。那会儿她烟不离手,抽的都是六块钱的软壳黄骆驼,心里憋着一股子劲不愿意显出女生气,觉得那样就不酷,她自己是这么说的。她对着玻璃的反光抓抓自己往一边倒去的短发,耸耸肩,看起来像是暂时对自己那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感到满意了。
“你还打算再文么?”我问她。
“暂时没有这个愿望。”她说,“我以前总是以为,在皮肤上文了图案,那些相关的记忆就不会再被忘记。可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算碰到很糟糕的文身师,图案也要隔很久很久才会模糊起来,但记忆迅速就模糊了。我自己都吃惊,怎么把那么多事情都忘记了,再也想不起来痛苦的感觉了。不甘心呢,我有时候想,是因为还不够痛么,痛得还不够刻骨铭心么?”
可是到底怎么样的痛才叫刻骨铭心,很难吧。我想。
我给她看手背上的疤,是高三时在马路上与男生飙自行车摔的。当时只是手掌青肿,站起来拍拍屁股就继续骑回家了,以为是伤到筋骨而已。因为怕家里人责备,还随口编造了根本不值得相信的谎话。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才发现是骨折了。时间隔了太久的缘故,骨头断开的地方已经斜插过来,自行愈合,所以不得不做了个小手术。局部麻醉,也做了差不多文个文身的时间。之后裹着纱布去参加各种毕业时节的重要考试。这样等到拆线的时候,手背上留下一道五厘米长、歪歪扭扭的伤疤。最初的一两年时间里,伤疤都是深红色的,每个刚认识的人都会小心翼翼地碰碰久已愈合的伤口说,疼不疼。当然不疼了!我心里想。
再过两三年,伤疤的颜色就变浅了。其实我自己早就已经忽略了它的存在,对我来说,与指甲盖上的蛔虫斑或者肉刺并无两样,生来如此似的。而新结交的朋友,依然总会问起。有的人一惊一乍,有的人犹犹豫豫。我就随心所欲地解释着,时间过去太久以后,自己都混淆了最初那个摔断手的夜晚是怎么回事。只记得自己在傍晚的马路上飞驰,春天,临近晚饭时间,黑夜好像依然比白天长,我使出一种疯狂的劲头与旁边的陌生男孩飙车,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跌下来的。但是朋友们总会煞有介事地摸摸那道伤疤,说,现在还疼么。
其实总有些后遗症的,像是阴雨天会有些酸痛,毛巾没有办法拧到干。但哪怕如此,大部分的时候并不会想起这道伤疤,自然更不会在乎它是不是很难看。不过就是懒得再去解释了。后来也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去文身,为什么要文棵树苗。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关心为什么,他们只是没话找话而已。
微微也摸摸我的手背。我想起当时照的那张X光照片,照片里我手指的每根骨头都那么细,好像稍微用点力就会断,岌岌可危,但其实这些年来它们也都是好好的,没有看起来那么脆弱。我以为她要问我什么,我有些担心她要问出跟他们一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好痛苦。”但是她这么说,说得我措手不及,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开一个玩笑。
“嗯?”我含糊地回了一句。
“真好笑,我这样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好笑。傻逼们才会问我为什么痛苦,我知道你不会问的。反正我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这会儿能说出来让我觉得好受些。”她说,像是在说件什么高兴事儿,或者是其他人的事儿。说完她用两根手指把烟屁股弹出好远。是啊,真的是这样的,我想,什么都没有发生,却觉得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
然后我们俩继续挨在一起走路,我脖子上文身的伤口蹭到衣领,有点疼,我不时得腾出手去拉一下衣服。这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大肆与人谈论痛苦,好像痛苦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甚至直接把这两个字说了出来,说得那么响亮,坦然自若,嘻嘻哈哈。夏日傍晚的太阳失去了一些温度,可是我们依然淌着汗,半途停下来买了两朵湿漉漉的白兰花。从今往后,都不会再有过这样的时刻。
肆 ◇
吃过午饭以后,我赶在妈妈起身前,先收拾起碗筷,拿到厨房去洗。一会儿她也进来,我转身让她,她则踮脚侧身从我旁边的架子上取下抹布来。再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于是我站到旁边,把水池让给她搓洗抹布。厨房其实很窄,挨着两个人的话就显得有些局促。我空举着两只手,惟恐洗洁精泡沫滴在地上。空气变得黏稠和僵硬,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关节咯吱作响。为什么不说些什么,我很想开口说些什么。但我也怀疑那些话语从我嘴里蹦出来以后,是否只会尴尬地滞留在半空中。
她洗了很长时间,像是也在犹豫什么,然后她把水龙头关了,顿时整个厨房安静得只听得到冰箱的压缩机嗡嗡作响。
“等会儿有空帮我染头发么?”她问我,这是这些天来她第一次主动与我说话。
“当然啊。”我赶紧说。于是她把抹布挂回架子上,又把水池让出来给我。我松了口气,再次把水龙头打开,耐心地把每个碗碟都冲洗干净,沥水,挨个儿放进消毒柜里。
其实在我回来之前就已经告知她,我并不会在家里住太久,所以托运回的十来个纸板箱也没有必要拆封。我没有用委婉的语言来跟她说起这些,尽管这么听起来确实冷酷无情,可是一时间又没有更好的沟通方法。我当然理解她对我的气恼,以及因此而带出的难过伤感,而我与她一样难过,只是我无法表达。
我的房间还是维持着我走之前的模样,就是那副中学女生房间的模样。九十年代时曾经很时髦的组合家具,现在还看得出努力保养的痕迹。墙上干干净净,只有一张我高中时在公园照的照片,青春期女孩特有的与整个世界犯别扭的神态。在我回来以后,她特意为我添置了一张梳妆台和一盏会在夜间闪出星星光芒的台灯。其实她从来不会直接表达爱,她甚至出于一种类似羞怯的情感而故意表现出冷漠。因此她也不会流露出怨恨、不满,她几乎从不宣泄。她绝不会像某些母亲那样哭闹、撒泼、哀求。但她会去买这样两件与整个房间格格不入的玩意儿,散发着簇新的家具气,像是在沉默地抗议。我每看一眼,就心碎一点。
我慢慢把厨房收拾干净,没有放过桌面上的水渍,完全是在磨蹭时间。等好不容易走出厨房,染发膏都已经调好了,装在小碟子里。她甚至已经对着镜子努力完成了刘海附近力所能及的部分。见我出来,便把一次性手套和围兜递给我。她的头发白得很早,她们那一众姐妹都是如此,所以几年前我就开始帮她染发,差不多一两个月一次的频率,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免不了要再加染一次。这活儿完全不用再交代,我的手艺非常熟练,随手拈来。
她的发质与我相像,又卷又硬。年轻时她烫着一头卷发,那时我们还蜗居在老屋里,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她都对着面破破烂烂的镜子把刘海吹得高高耸起。平日里我与爸爸去她上班的工厂附近接她,也能看到她骑自行车潇洒地迎面而来,连衣裙裙摆飘飘,刘海都被风吹得往一边倒去。我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剪了短发,从此几乎再也没有往头发上花过什么心思。这些年来,她对衣物也逐渐失去了兴致,稍微尖一些的皮鞋她穿着脚痛,所以家里多是那些笨拙的圆头厚底鞋。我送过她很昂贵的皮包,她嫌弃那包是真皮的,太贵重,一直搁置不用。最常拎着的却反倒是我大学里买给她的一只人造革包,拎手几乎裂开。她有自己执拗的审美,条条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