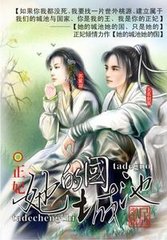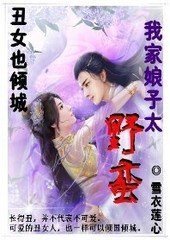荒芜城-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事。”我说,好像他真的是在跟我道歉似的。
他完这些以后,我们俩都像是松了口气。好像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难过,我甚至并没有真的哭出来,没有像我们之前无数次争吵中表现得那么歇斯底里。我竟然依旧平平静静地握着电话线,感觉自己冷酷、坚强,像绿野仙踪里那位没有心脏的铁皮人。我能够听到他在那儿呼吸的声音,能够想像他拿着电话,站在窗边,外面是中学的篮球场以及昏黄的天气。我听到他拿出打火机,噌的一声点了根烟,于是我也点了根烟。
他在那头说喂,我说喂。他又说喂,我说喂。接着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再过了一会儿,他像往常一样失去了耐心,把电话挂了。
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在这儿也结识了一些朋友,有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吃火锅,逛街,也很不错。但如果晚上就是世界末日的话我是否愿意与他们待在一起?有些累啊,还要努力制造各种话题,维持一种彼此之间友谊的错觉。我想。
我趁着还有些天光去了次菜场,气喘吁吁地拎回来整整两塑料袋的蔬菜、鱼、各种豆制品。其实我从来不曾与阿乔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太阳慢慢沉下来,雾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他每天都与小湘一起吃晚饭,她不会做饭,只会炖些简单的汤,再从熟食店里买回些冷菜。大部分的晚饭时间他们都在楼下一间小饭馆度过。这间小饭馆夹在小区的两幢楼中间,正好是我从来不会经过的死角,阿乔也向来对此避而不谈,从未对我描述过那儿的样貌。在我的想像里,那儿大致就跟其他北方的街边小饭馆一样,挂着塑料帘子,冬天的时候再隔上层棉毯。老板掌勺,老板娘收钱。柜台后面摆着二锅头和整箱的燕京啤酒,但是阿乔喝燕京会头痛,所以我就在想像里更换成青岛啤酒好了。他们身后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新闻,老板会送上一两碟自己腌的泡菜、毛豆。他们大概不会说很多话,所有那些长年待在一起的夫妻,总是安静地坐在饭桌上各自吃自己的菜,偶尔一起抬眼看看新闻。等到结账的时候,与他们相熟的老板自然会抹掉一些零头。
我在阿乔家的鞋柜上见过那间小饭馆的外卖单,印在粗糙的白纸上,上厕所的时候我拿在手上仔细读过,他们常常点的菜是什么呢?他们喜欢吃木须肉么?我在冰箱里看到过他们带回来的打包盒,裹在塑料袋里,掀开来,里面是吃剩下的回锅肉,油都冻起来了,浮在上面白花花的一片。
我们从来不问候对方晚饭吃了什么,这段时间,我们都觉得还是草草跳过比较好。就好像他俩都凭空从世界的某个出口消失,而我其实也很享受一个人的晚饭。做菜全凭自己喜欢,时间上更不必迁就别人。有时候坐在桌子旁边,什么事情都不做,不开电视,也不看书,甚至没有心事可想,就这样专心致志地一口口吃,可以吃上很久。只是常常菜做得太多,又不愿意隔夜再吃,就统统倒进马桶冲掉。
而现在当我手里拿着一大捆洗过的蔬菜打算要下锅的时候,想起来油用完了。只好停下来,去楼下的烟杂店里买。正是晚饭时间,烟杂店那一家人正在吃饭,他们背对着我围坐在临时搭出来的小桌子前,一大盆红烧肉和一大盆丝瓜汤。我从没见过他们吃饭的样子,平日里过来,店里常常只有一两个人,死气沉沉地坐在柜台前,看电视连续剧,嗑瓜子或者打瞌睡。而此刻虽然他们并不说话,却大口吃饭,碗筷欢快地碰撞在一起,电视里在放地震的新闻,黑白一片,但是没有开声音,也没有人抬头看。我竟然感到自己的出现打扰了他们的好时光,简直想要悄悄退回去。
那家人十六七岁的女儿站起来舀汤,转身间看到我,不好意思地放下碗筷,用手背擦擦嘴巴,急忙朝我走过来。这会儿,老板也注意到我,回过头来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就把注意力放回到了饭桌上。我有些过意不去,除去买了瓶油,又买下些根本不会去吃的零食。在等着找零钱的间隙,女孩靠在门框上,望着外面,眼神久久地停留在远处。我不由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起风了,卷起地上小小的尘埃。
“外面的风可真大。”她说。
“可不是么。”我说。
这是个非常漫长的夜晚,我坐在茶几边久久地吃饭,喝完整瓶的桂花酒。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电视机整夜都开着,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放相同的救灾新闻,不时出现黑白的画面,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在哭。刚开始我支棱着耳朵留意外面的动静,可这无疑是个比平常更加安静的夜晚,我有时站到窗口看一眼,只有一盏路灯亮着,一些虫子无声地往上面扑去。我知道世界末日不会来临,死从来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而我第一次感到接下来的日子无以为继,漫长的等待叫人痛苦万分。
中间妈妈又打来过电话,我把电视机开得很响,告诉她我与同事们在一起,我们正在看新闻里的直播。我或许睡着了一会儿,但是又不断醒来,每次醒来时间就只过去了一两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只有二十分钟。四肢酸痛,疲惫不堪,像在梦里长途跋涉。
这样等到第二天傍晚,我终于无法忍受,套上外套出门去找阿乔。
我不知道自己要找他做什么,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间我或许会同时撞上他们俩,但那种要立刻见到他的愿望像火一样四处燃烧、爆炸。我走在路上,被风吹得几乎要流出眼泪。马路上的一切都秩序井然,二环上的车堵得死死的,但没有人按喇叭,大家都安静地等待着,有人摇下车窗抽烟,有人走下车来,松松皮带,望向前方。
阿乔看到我有些惊讶,但房间里就只有他一个人,拉着窗帘,静悄悄的。他没有说话,侧身让我进来,在我身后关上门。我脱了鞋,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来。然后我低下头,不看他,盘算着此刻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有过很多个和解的时刻。我记得有一个彻夜未眠的清晨,我们俩终于决定不再继续争吵,而是坐上最早班的轻轨去郊外爬山。冬天,轻轨上几乎没有人,我们站在两节车厢中间,紧紧地搂在一起,靠着窗口。外面很冷,窗户上沾着水汽,整个北京都还没有苏醒,车开得很慢很慢,不知是不是我们的错觉。我现在都想不起来那座山的名字,阿乔说很多年以前,他刚刚来到北京时曾经就住在山脚下,与很多人一起租住着一个四合院,常常断水断电。那会儿很穷,他们几个人煮上一锅番茄鸡蛋挂面,能吃整整一周,夏天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出去打水,冬天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去澡堂子里泡澡。我想像这幅场景,不由就笑起来。
爬山的时候,他一路拉着我的手,我们经过大片大片野生的大麻田,爬到山顶,坐下来抽了两根烟。很冷,风很大,天气阴沉,看不到日出。倒是忽然从四周涌来浅褐色的雾气,像是轻柔的洪水把我们浸没。
我常常觉得我们就应该是如此与世隔绝的,但是此刻我坐在沙发里,他坐在我对面一把椅子上,我又不免对自己产生怀疑。我无法抬头去看他的眼睛,好像他的眼神会迷惑我,让我无法做出判断。所以我只是看着他的脚、小腿、膝盖、他的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怎么了?”在沉默了许久以后,他问我。
我没有说话,转过头去望向其他地方。于是他点了根烟,看着我,房间里太安静了,他每抽一口,我都能够听到烟叶和卷烟纸燃烧时发出的嘶嘶声。
“说话。”等他掐灭了这根烟,又忍不住催促我。
我依然没有说话。他向来仇恨我的沉默,我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坐在车里,坐在饭馆里,他都希望我们始终处于一种交流的状态,哪怕不说话,我们可以望着彼此。并且我们几乎每天都做爱,我们或许都彼此担忧着只要一天不做爱,我们的感情就会折损,甚至消失。我们对外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俩的事情,因此我们也从不谈论其他,我们只对彼此感兴趣,只谈论彼此,现在、过去,所有角角落落和细枝末节都不肯放过,一定剥去对方的皮,饮到对方的血,才能觉得放心。
我能感觉到他开始生气,他在房间里不耐烦地走动,叹气,把东西放下来,又拿起来。我试图发出些声音,却觉得经过这漫长的夜晚,喉咙仿佛也被锁住。我担忧着自己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我需要看到他,但此刻我又意识到,看到他也令我痛苦万分。
我们像这样僵持着,我浑身的关节都开始疼痛,感觉唇齿间要长出青苔来。而外面的天色再次不可挽回地暗下去。阿乔站起来,他没有再说话,只是从卧室里拿起外套穿上,又把烟盒和打火机放进口袋,我想他再接下来就得去拿钥匙了,但是他没有,他只是站在离我不到一个手臂的地方,双手插在兜里,这样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这会儿已经到了他去小饭馆与小湘吃晚饭的时间。
我终于抬起头来,看看他,房间很暗,他的整个脸都被浸在阴影里。他叹口气说,他得要走了。他没有解释说要去哪里,好像我理应知道并且接受似的。我又低下头,并没有挪动,我从未哀求过他,但是这个时刻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得走了。”他又说了一遍,像是在告知以及威胁。
于是我站起来,扬起手扇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我僵在那儿,只感到手掌心里一阵阵针刺般细小的麻痛,这场面让我自己都觉得可笑,我突然之间明白为什么我坐在那儿不敢挪动,只要一挪动,一个细小的表情,一句闷哼声,就会彻底暴露我的内心。那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内心,除了嫉妒、恨意、占有欲,几乎什么都没有再剩下,我甚至感觉不到爱。没有爱。
接下来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失去了控制,我把自己像个布袋一样地朝他撞过去,他把我推开,我绊倒在沙发上,然后又爬起来,紧紧抓住他的衣服,我无法判断这样到底是想弄痛自己,还是想弄痛他。我不断地被他推开,又再神经质似的撞向他。我的脸上全是泪水,但是心里空荡荡的。我能看到他对着我大喊大叫,他的脸就凑在我跟前,我们彼此仇恨的程度,与做爱时彼此热爱的程度并没有相差多少。
最后他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把我举起来,然后扔到地上。我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全部撞向地板的声音。然后他坐回到椅子上,抓着自己的头发,而我在地上看着他,房间已经黑成一团,只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些微不足道的月光,浓重的阴影淹没了这个房间,淹没了我们俩。这会儿,他的手机振动起来。一开始我们都置若罔闻,它就在鞋柜上,闪着荧荧的光,它兀自振动了一会儿,停下来,接着又振动起来,越来越快,像是在呼唤。
“操。”他猛地站起来,把手机按掉。然后他骂骂咧咧地把扯坏了的连帽衫脱下来,换了身衣服,再把烟盒和打火机都掏出来放进衣服口袋里。这回他脚步坚定地往门口走去。于是我也站起来,走到门口,蹲下来穿鞋。鞋带扣得死死的,我拼命扯了好几下都没有办法扯脱,只好把鞋跟踩踩扁,生怕来不及。我看着他锁门,顺便提上一袋扔在门口的垃圾,然后我们一起挤进电梯,与楼道里其他吃完饭正要去散步的人挤在一起。他们带着热烘烘的生活气息,啧啧地说起地震的新闻,有的人手里还捏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头版的照片里是一整片废墟。说完这些以后他们用比以往更大、更明亮的声音彼此打招呼,甚至朝我们这两个陌生人点头微笑。我们简直被这样的热闹与温暖吓坏了,站在角落里不敢挪动,惟恐被他们发现,其实我们从心底来说已经没有了生命,只是两具尸体而已。
走出楼道以后,我本该向右拐,走出小区,穿过二环上的桥,再抄一小段近路回家,这是我几乎每天都要走的路。但是那天我没有,我跟在阿乔身后左转,走了一小段路。没有路灯,平添凉意。他就这样急匆匆地走着,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也停下来,在黑暗中试图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他气急败坏的,不像他平常的样子。他再往前走了几步,我也又跟了几步,他紧张起来,我知道,因为他紧张的时候就喜欢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并且开始抖腿。“你到底想怎么样。”他说。
是啊,我到底想怎么样,如果我知道我想怎么样、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否就算是解决了。我们是否就可以解脱彼此之间的折磨。但是我从未如此刻这般迷惘,梦境尾随着我进入白昼,几乎要摧毁我。我们沉默着,站在一条窄小道路的中间,僵持。旁边有一对中年夫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