鸾归桐-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场风寒之后,一样接一样奇怪的事接踵而至。
偏偏还想不分明,说是先知吧还不完全是,说不是先知吧那又能是什么呢?
她心如乱麻,烦躁不已。
郭圣通叹了口气,懒得去想。
唤了常夏同羽年进来服侍她梳洗后便往锦棠院去了,今日她答应了弟弟要过去的。
心下的结一个接一个解不开,日子却还是一天又一天平静如水地在往前滑。
她能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一点点解开这些结。
春风和煦扫在她脸上,她迷茫的目光慢慢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很奇怪的是,她昨夜没睡好应该困倦的很才是,但却觉得精神抖擞,一点都没有要犯困的意思,心间也愉悦轻松的很。
她一路上始终抿觜轻笑,偏偏自己还没察觉。
还是在锦棠院外碰着母亲身边的红玉,她无意间说了句天气好是叫人心情好,郭圣通才反应过来。
她蹙眉不解,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自己高兴什么。
因为要和弟弟一块放木鸢吗?
那也不用这般情不自禁地一直笑吧。
脑海中蓦然闪出昨夜那个奇怪的梦境中冲她笑的男子身影,她吓了一跳,深吸了一口气才把关于梦境的回忆压下去。
她劝慰自己:自怪烧后,她就很奇怪,所以这个莫名其妙的梦也就不奇怪了。
她脚下放快,须臾间就进到了锦棠院里边。
郭况很早就到了,在廊下摆弄着头天和郭圣通一起选定的墨鹰木鸢。
母亲站在一旁,不时笑着应他句。
郭圣通心间如阳光照进,温暖不已。
她提起裙摆,笑着走上去。
☆、第十四章 相术
弟弟郭况眼尖转头就见着了她,把木鸢丢了跑上来,围着她“姊姊”地一直叫个不停,亲热极了。
母亲都有些眼热,和郭圣通笑道:“这孩子,自小就最黏你。”
郭圣通就上前搂着她的胳膊道:“我小时候最黏你还不够?”
母亲便笑了。
一家三口温馨简单地用过了早膳后,母亲就去了正院料理家事,把姐弟俩留在花园中玩耍。
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
风也恰到好处地不大不小,正适合放木鸢。
郭圣通和郭况对此都满意的很,郭况一本正经地同郭圣通说这是天公作美,逗得她笑了好一会儿。
木鸢很快就随风放了上前,越飞越高,仰头望去宛如活生生的苍鹰翱翔在空中般。
白晃晃的阳光刺的人睁不开眼,郭圣通抬手遮额眯着眼看去,只见那木鸢越飞越高,几乎快变成一个小黑点了。
郭况的笑声就没停下过,伺候他的侍女家人子围在他身边,不时叫着“公子,放线放线——”、“公子,风来了别怕,拽紧了就行了”。
一片欢声笑语,随着春风吹出老远去。
庭中西南角种着一大片竹林,正值春来发新竹的时节,整片竹林生机勃勃、青翠欲滴。
风一来,吹动一地斑驳树影。
挨着竹林种了整整一面墙的贴梗海棠,枝秆丛生,朱红色的花朵紧贴梗上,密密麻麻大片大片地开得深沉。
阳光漫洒在花间叶上,愈发显得海棠花剔透水润。
趁着天气晴好,廊下摆了一溜牡丹花盆,魏紫、黑花魁、姚黄、西施等等名贵品种俱在其中。
深绿色二回三出互生的披针复叶簇拥着无数花苞,在风中微微摇晃着枝杆。
绿叶红花,辉映着雕梁画栋,在蓝天下晃动反射着灿烂的日光。
极目远望,亭台楼阁俱隐没在绿荫深处。
侍女们说笑的声音越墙而过,断断续续地也听不真。
这安逸和乐,仿佛能一直延续下去。
郭圣通深吸了一口弥漫着花香的空气,心下想但愿能一直这样,但愿这不是她的奢望。
午膳时,疯玩了一上午的郭况饿坏了,就着红枣羊肉炖萝卜同鲫鱼豆腐汤便用了两碗饭。
母亲怕他小人儿积了食再消化不了坐了病,怎么都不肯叫他再吃。
“按说让你两碗,都多了。”
郭况便悻悻然地起身,冲母亲跺脚:“那我去念书了。”
母亲瞪他,他知道母亲并不是真的生气也不怕,转向郭圣通道:“姊姊,姊姊——你说的我认真念书十天,就能玩一天的,是吧?”
他虽然是朝着郭圣通说,眼角余光却一直瞟向母亲。
郭圣通哪还能不明白,便向母亲解释道:“放木鸢时我答应他的,我想着劳逸结合才能叫况儿更学得进去。”
母亲想了想,“怎么叫认真念书呢?我们总得有个标准,每天完成我布置下来的功课就叫认真念书,只有这样才能一旬而休。”
郭况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应了声好就跑了。
母亲就道:“况儿要真能坚持下去,倒也真是好事了。”
郭圣通好笑地道:“阿母,您总是担心况儿不学好,怎么就不担心我?”
母亲神色认真起来,满是自豪地道:“你就没叫我操过什么心,我担心你干什么?”
郭圣通失笑,心血来潮地道:“那我能不能也像表哥一样出门游学?”
表哥刘得去岁出门游学了大半载,叫她和弟弟都羡慕的不行。
听说她想游学,母亲想都没想,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郭圣通早就想到会是这般局面,也没有什么好意外失落的。
她止住母亲劝说她打消念头的话,宽母亲的心。
“我知道,我就这么一说,不是真要去。”
母亲见她神色认真,不似作伪,方才松了一口气。
又怕她失望,便道:“你想学什么也可以在家学啊,阿母给你请讲席进来。”
郭圣通听着母亲这么一说,心念一动,觉得倒真应该再多学些什么。
她的先知,能瞒一时却瞒不了一世。
尤其是在朝夕相处、血脉相连的亲人跟前,哪能时时刻刻保持住警惕心不出错?
学奇门遁甲的话倒是能最好地把她的先知解释为预知,但奇门遁甲太难不说且是帝王之学,她无端怎么会要学这个?
她眼珠一转,不如和母亲说学相术。
真定曾来过一个神算子,被无数达官贵人引为上宾。
便是舅舅都设宴宴请过他,表哥那时还闹着要拜师。
大舅母不许,后来那神算子云游走了,表哥气了好长时间。
她望向母亲,“阿母,我想学相术好不好?”
母亲一时愣住,她完全没想到女儿会提出要学相术。
想说答应吧,但哪去给女儿寻真才实学的人来当教习?
似那等能窥破天机的人,不说轻易遇不着,就是遇着了如何肯平白无故地传授?
若是随便糊弄一下女儿,那又怎么行呢?
再说,方才已经叫女儿失望了一次,怎么还好拒绝?
郭圣通看出了母亲的犹疑,便挪到母亲身旁搂着她的胳膊撒娇道:“大舅母不叫表哥学,表哥难过了很久,你肯定舍不得叫我难过是吧?”
她声音娇憨甜糯,清澈天真的眼神中满是哀求。
母亲莞尔,“我哪说不行了?”
她把担忧和郭圣通一一说了,而后同郭圣通商量道:“桐儿若想学,一时半会地便只能自学,等什么时候碰着那等真人了,母亲再为你去求问。”
郭圣通没想到母亲犹豫的不是要不要让她学,而是怎么学。
她心下彷如有热流滚过,温热一片。
她抱住母亲道:“好,我也没想学出什么名堂来,就瞎学玩玩。”
母亲拍了拍她的手,颇有几分无奈地道:“好了,好了。怎么大了倒又撒起娇来了。”
郭圣通失笑,母亲明明就很喜欢她这样嘛。
她抱得越发紧了,“你是我阿母,不和你撒娇和谁撒娇。”
母亲果然被哄得更开心了,明媚的笑容挂在唇边就没下去过。
郭圣通想了想,又道:“母亲,我还想学医术。”
她心下已经肯定她身上的种种异常,不止是先知可以解释的。
☆、第十五章 岐黄
所有的异常都是从那场诡异的高烧后才出现的,她想好好学学医术,没准就能找着缘由所在。
这下母亲应承的就没那么痛快了,“巫医乐师百工,俱属贱业。
好好地,你学什么医?”
医家虽行的是救死扶伤、妙手回春之举,但史书传记中鲜见对名医的记载不说,自古以来更是地位卑微,医家动辄便性命不保。
《吕氏春秋》中便记载了文挚殉医的故事。
文挚是战国时期宋国名医,医术高超。
齐闵王患病,使人请文挚诊治。
文挚详细诊断后,同齐太子说齐王之病需以怒气治之,他担心治好之时便是他丧命之时。
齐太子哀求不止,并言愿以自己和母亲齐王后的生命来为他求情。
文挚便应了,以失约、无礼等种种行为来激怒齐闵王。
结果,齐闵王病好后不顾太子同王后哭求,大怒而杀之。
只是郭圣通却道:“贱业又如何?
如良医扁鹊,是不是声名始终不减,受尽怀念和尊崇?
我上次病时,您还叫人去扁鹊庙中去祭拜祷告呢。
再说了,没有医工来治我,我说不得就死了。”
母亲闻言愠怒起来,叱责道:“小孩子家家,不许动不动就说什么死字。”
郭圣通知道犯着母亲忌讳了,吐吐舌头,觑着母亲的脸色赶紧认错:“我就那么一说嘛,我再也不敢了——”
她顿了顿,试探地道:“可是,道理是不是那么个道理?”
母亲瞪她一眼,怒气不减。“惯会胡说,有什么道理?”
郭圣通知道她上次的怪烧着实把母亲吓得不轻,当下讪讪然不敢再说。
她和弟弟,从来都是母亲那道不能触碰的底线。
母亲深吸了一口气,心下平静了些,回身见郭圣通颇有些可怜巴巴意味地坐着。
又有些心疼,“好了,好了,再不许这般胡说了。
不吉利,知道吗?”
郭圣通忙点头,而后又怀着希冀。“那——”
母亲被她磨得也实在没脾气了,想想学点岐黄之术也没什么坏处,便道:“你若实在想学,便跟着家里的乳医先学着吧。
若是真学得进去,阿母再为你延请常安城中的名医。”
郭圣通心愿达成,欢笑着扑进母亲怀中。
“我就知道您最疼我——
我知道您不叫我学也是为了我好,而且我又不会真背了药箱去行医。”
她仰起头,望着母亲说道。
母亲的笑容不受控制地往上爬,女儿小来比这还能撒娇耍赖,稍微大了些才开始要装出个大人样。
刚开始她失落了很久,不过是想着女儿大了也是正常才觉得好受些。
但没想到女儿病了一场后,又和她变得亲近起来。
她想女儿是渐渐大了,懂事了,开始知道体谅孝顺母亲了。
从前哪会想着多学些什么呢?
于是,当晚母亲就叫人送了十匹布同两百两银子给乳医作为一年的束脩。
乳医惶恐不已,不敢接礼,亲自到锦棠院中来婉拒。
“女公子肯跟着婢子学岐黄之术,已然是婢子的荣幸了。”
母亲摆手,郑重其事地道:“既然是学艺,便要正正经经地拜师。
等十天后,她开始进学。
我还要叫她向你敬茶行拜师礼呢。”
乳医连说使不得,但母亲坚持礼不可废,最后她便只得应诺回去。
郭圣通在漆里舍很快也听说了还得向乳医行拜师礼的事。
她笑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乳医虽是她家的家人子,但向人家学其安身立命的本事自然得恭谨点,才能叫人家打心底愿意教她,而不是推不过不情不愿地教她。
她叫了人把家中关于相学和岐黄之书的帛书竹简全搬到了漆里舍来,把卧房旁边的侧厅收拾出来充当了书房。
没过两天,母亲又从外买了一车竹简回来。
全是关于相学和岐黄之术的。
郭圣通上午都在锦棠院陪着母亲,用过午膳后才回漆里舍来整理帛书竹简,闲下来便握着《太史公记》看。
十天的时光一晃而过,这十天中她都没有再做梦。
她觉得很安心。
睡得好,精神自然就更好。
翌日清晨她起了一个大早,洗漱更衣用了早膳后,便往东厅去
家里为她请的女讲席已经到了,见她来微微一笑问她是否大好了。
女讲席,姓文,闺名一个珍字。
听母亲说,文讲席从前也是官宦人家的千金,不过是后来家道中落,无奈之下才做起了教人念书的讲席。
郭圣通很喜欢文讲席,她温柔耐心的很,同母亲的性子很像。
她行了一礼,“学生叫女师担心了。”
文讲席笑着叫她坐下,“身体康健便好,今天我们开始讲左传……”
文讲席教她,并不像一般的女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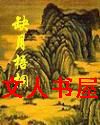


![(古剑同人)[古剑]梧桐砧琴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23/2358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