鸾归桐-第1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想,她不喜欢他行,可是他不能不喜欢她。
如果可以,她要做那个放弃他的人。
她不想被抛弃,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她的齿又咬上下嘴唇,她缩在毯子里双肩抖的厉害。
她尽量让自己无声无息地哭。
遇见他之前,她以为她够冷静够清醒。
可原来,她矛盾到她自己都看不懂。
倘若她置身事外地看自己的故事,她一定会骂自己傻,她一定会觉得她不会这样。
可是情之一字,最是难解,自古如此,她如何又能例外呢?
她狠哭过一场后,又躺了半天来平复情绪。
她倾耳细听了会,刘疆的呼吸声依旧平缓绵长,一时半会地应该还不会醒。
她蹑手蹑脚地下了地,尽量不弄出水声地绞了帕子来擦脸。
而后,她跪坐在梳妆台前,仔细地补了一遍妆。
嗯……
妆哭花了。
发泄过情绪后,她开始觉得刚刚的举动实在是太好笑了。
幸好,殿里没有人。
冷静下来的她还是坚持靠谁不如靠自己的观点。
毕竟,谁知道命运什么时候又一个急拐弯,把所有的一切一把就推到了原先的轨道上了。
现在,她所需要做的只有等待。
等真爱和两个姑姐一起来,等刘秀的反应。
刘向在《说苑·正谏》中说:“园中有树,其上有蝉。
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
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
她现在便是那只静观其变,进退自如的黄雀。
刘秀这天傍晚回到却非殿时,郭圣通正在软榻上陪刘疆玩,听着他回来的动静便交待羽年看着孩子,脚步轻盈地转到了侧殿。
刘秀正伸平了手让宫人更衣,一抬眼见着她眉眼带笑地站在门口,便招她过来。
她笑着上前,示意宫人退下。
她是第一次服侍他,弄得他高兴之余又有些紧张。
看着她笨手笨脚地忙活了半天还没弄完,他真想自己动手,麻利地穿完得了,但想着好不容易破天荒这么一次,他到底还是忍住了。
他唇角上扬,无奈地笑了笑,心道看来她今天心情是出奇地好。
她高兴,他也跟着开心。
左右,她这般喜怒反复无常,他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只要她高兴就行。
等她终于为他更好衣后,他余光中见着她额头上都热出了层细汗来。
他忙赶在她前面绞了帕子净面擦手,“饿了吧?我们用膳吧。”
天气冷,晚上上的古董羹。
片得极薄的牛羊肉在滚开的乳白色汤锅里打两个滚,夹出来蘸一口蘸料就能吃。
牛肉鲜嫩,羊肉膻香。
吃饱了肉便下几筷子香菇、菘菜等素的,滋味也是好得很。
吃得有些发撑了,最后再往里下点汤饼。
干虾仁枸杞红枣的汤底本就鲜得人掉眉毛,又涮了牛羊肉和青菜香菇,味道早熬得浓郁香醇。
汤饼煮得浸足了滋味捞起来,爽口味美,自然得吃上一碗。
这么一顿下来,郭圣通自然是吃撑了,弄得她都不敢抱刘疆了。
他现在有劲的很,她有些时候真闹不过他。
但刘秀也不让她坐着,他右手一只手把刘疆抱在怀里,另一只手便来牵她:“起来散散,消消食。”
虽然觉得绕着屋子散步的行为有些傻,但她还是把手递给了他。
这么多人看着,不能不给陛下面子啊。
他的手比她大多了,她被他握得紧紧地,殿里暖气又足,他的手很快出了汗,贴在她手背上怪难受的。
走了没有半柱香,她就挺不住了,想抽出手来。
☆、第两百四十七章 降王(四更)
他大概以为她是想偷懒歪回榻上去,她越动他握得便越紧。
她见他单手抱着刘疆,又怕她使劲挣扎他光顾着按她,再把孩子摔了。
可是,被这么包在他手里又实在难受。
于是,她轻轻地挣扎。
一下,两下,三下……
她以为刘秀会知道她不舒服然后放开她,谁知道他叹了口气满脸无奈地转过来看了她一眼。
那意思分明是在说:听话,别跟小孩子一样耍性子。
她咧了咧嘴,决定有话直说:“放开我,你手太出汗了……”
他楞了一下,然后忙不迭地放开她,顿了顿道:“再走两刻钟。”
她抿着嘴忍笑点头。
她不知怎么,此刻猛地想起了刚成婚时。
她晚膳喝多了汤,夜里被憋醒又不好意思下榻去,等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还被刘秀死拽住。
真是现在想起都觉得尴尬的不行啊。
她的笑到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弄得刘秀和刘疆父子俩一起回过头奇怪地看着她。
终于散完步后,刘疆也被晃得眼皮发沉了。
郭圣通赶紧叫人往他的小浴盆里放水,然后三两下就扒了他的衣服,把他泡进盆里给他洗澡。
刘秀站在一边从头瞧到尾。
这照顾儿子时手脚又麻利又稳妥,怎么到他这就笨得腰带都不会系?
还是儿子重要啊,他有些发酸地想。
等郭圣通哄睡了孩子后,他让宫人们都退下去,想和她好好聊会天。
可聊什么呢?
他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最后不得不承认就聊天话题来说暂时只有一种——政事。
他不知道她爱不爱听,虽然她每回都听得很认真。
他想,等大姐和小妹来了就好了。
女子间能聊的话多,她们之间亲近了,连带着她和他也会亲近的。
郭圣通盥洗过后,卸了钗环,心情愉悦地撩开床帐,想着好容易熬完了一天终于可以睡觉了。
可——
他这么目光炯炯地看着她干嘛?
还有,疆儿呢?
他拉她上榻:“地上冷,快上来。”
郭圣通撇嘴,心道你这么说,壁炉和火墙会哭的。
她问他:“疆儿呢?”
“朕想和你说会话,叫常夏带到侧殿去睡了。”
她立马想起真爱贵人,心道这会就要摊牌了?
她很快就想好了。
等他阐述完他和真爱间凄美动人的故事后,她就微微一笑:赶紧接过来吧,我不介意,当然不介意。
她上了榻躺下,满怀期待地盯着他。
“更始降赤眉了。”他首先用一句话概括完整件事后,然后开始细说。
郭圣通楞了下:啊,说这个啊?
不过刘玄的下落,她确实也好奇着。
“长安城破后,刘玄单骑策马出城,朕不是还下了旨意寻他吗?
可一直也没消息,后面又忙着攻洛阳。
等再知道他下落时,他已经投降赤眉军了。
原来他出长安后,一口气跑到了高陵右辅都尉严本那。
朕曾经和严本共事过,知道这就是个口蜜腹剑的人,但偏生就因为会说话能邀功让刘玄拿他当心腹看,弄得刘玄走投无路了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
刘玄这步棋走的真是臭死了,他要是趁乱跑到什么穷乡僻壤里躲起来,还能安安稳稳地活到寿终正寝。
可,他竟去了严本那。
严本唯恐赤眉军因他收留刘玄而迁怒于他,再叫他受了池鱼之灾,还不如献给赤眉讨个好。
于是,他一面使人去和赤眉联络,一面派重兵看守刘玄。
结果,先等来的是刘盆子长兄刘恭。
王莽篡汉后,夺了其父刘萌的爵位,刘恭、刘茂和刘盆子三兄弟便沦为了平民。
后赤眉军破式县后,将刘恭及他的兄弟刘茂、刘盆子抓去充作了杂役。
去年九月,更始帝入洛阳后招抚四方。
刘恭随樊崇到了长安,因为他是汉室宗亲,少来又读过几本书,为刘玄欣赏,得以重新恢复了祖上的爵位。
后更始帝和赤眉闹翻,刘恭却始终留在更始身边。
到了今年六月,赤眉军用抽签的方式选中了刘盆子为帝。
消息传到长安后,刘恭虽事先毫不知情,但为了避嫌还是自投入狱。
现下听闻更始投奔了严本,忙越狱而追。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根本无法在重兵看守中救出更始。
樊崇见严本信后,下书称‘圣公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
真是时移世易啊,从前赤眉为更始卖命打仗,更始连粮草都不给人家。
如今被人家赶出了长安城,给出了个二十日的期限就吓得不行,刚接着信就慌忙派刘恭代表他去受降。
双方谈妥后,很快就在长乐宫举行了受降仪式。
赤眉军诸将估摸着是一见到刘玄,就又想起了从前的屈辱,于是当场翻脸,罪责更始,拖下庭中欲杀之。
刘恭和之前代表赤眉接洽受降的谢禄皆以为不妥,大丈夫一言九鼎,既说了刘玄若降便封其为长沙王,岂能出尔反尔?
但背叛了更始的王匡、张卬、廖湛、胡殷等更始旧将无论如何也不答应,说得赤眉诸将也火气往上涌,纷纷力主杀了他。
刘恭求情于弟弟刘盆子,可刘盆子这么一个傀儡皇帝哪做得主?
眼看着闪着寒芒的利剑就要落在刘玄脖子上,刘恭大急,拔剑欲自刎:“臣诚力极,请得先死。”
虽说刘盆子就是个摆设,但也不好真叫刘恭这个皇兄血溅七步啊。
而且,思来想去,终究觉得答应好了的事又反悔,岂不为天下人耻笑?
于是,樊崇封刘玄为畏威侯。
刘恭认为原先说好了封长沙王的,不肯就此罢休,复为固请。
樊崇估摸着觉得反正也不杀刘玄了,封侯封王都差不多,左右也只是那么个名头,便也从了。
刘玄从此实际上便做了阶下囚,但听说他过得还挺快乐的。”
刘秀说到最后,鄙夷之色毫不遮掩。
也是。
依着他的心性来说,换了是他,与其如此受尽屈辱地活着,还不如自杀了断。
但刘玄要是有这份骨气,那他也就不是刘玄了。
郭圣通看了眼刘秀,忍不住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道:“我怎么觉得陛下有些遗憾呢?”
他笑,而后认真地点头。
郭圣通看着他笑,止不住有些心酸,她想他心底定是难受极了。
威名赫赫的刘縯惨死在这样的小人手里,他一定不甘极了吧。
偏偏,这小人还活着,还心安理得地受了长沙王封号后依附着赤眉军活着。
她低声道:“这样的人,活着和死了没区别。”
他点点头,他知道她是在安慰他。
可他还是缓缓道:“朕相信,更始叛将不会容许他活太久的。”
她忍住鼻酸,点头道会的。
☆、第两百四十八章 摆件
原先总是缠磨着郭圣通的梦境,在她成婚后渐渐沉寂下来。
近半年来她所做的关于前世的梦,屈指可数。
她不知道原因,但梦境的确鲜少再打扰她了。
它就像个跋山涉水后终于抵达目的地的旅人,风霜满面,疲惫不堪,倒在那一句话都不愿意再多说了。
新婚夜它那尖酸刻薄的讥讽,竟像是许久之前的事了。
是因为命运改变了,它不再具有发言权了?
还是因为它时常见着刘秀又勾起了从前刻骨铭心的疼痛?
她虽然就是它,但到底又不是它。
她在黑沉沉的梦境中低声叹息。
她不知道,在梦境的尽头,有一个孤傲身影站在那。
浓墨般的黑暗隐去了她的容貌,却出乎意料地把她身形的轮廓勾勒地异常清晰。
她似是听到了郭圣通的低叹,转过身来投过一瞥。
假如这时有一束光照进,就能看着她眸中戾气全无,笑意清浅,温柔至极。
可再一转头,笑意敛去,悲伤哀切愤恨种种情绪又浮上了她的唇边。
一夜酣睡,郭圣通晨间醒的很早。
身侧早已空荡荡了,只有她臂弯里的刘疆依旧睡的香甜。
她听常夏说,刘秀近来都是卯时初天还未亮便起身了。
多地同时用兵,又有纷杂内政,他恨不得一个人掰成八个用才好,更恨不得一天能有三十六个时辰。
大舅曾说,一个上位者若肯勤奋至少代表他在用心。
接下来所要注意的,就是前进的方向有没有跑偏。
说到大舅,母亲前段时间来信叫她放心。
母亲说对于放弃河北之王这种正确却无奈的做法,大舅并未思虑太久便答应了。
不甘又如何?
忿懑又如何?
不依不饶地,对彼此都没有好处,还不如匿瑕含垢,以待将来。
毕竟,只要刘秀能掌控住整个天下,真定刘氏作为后戚足有三世风光,为何非得在当大事未成便急着计较呢?
有些时候,失去了才可能真的得到。
至于舅母虽颇有微词,但到底是高门贵女,识大体,顾大局,连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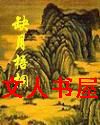


![(古剑同人)[古剑]梧桐砧琴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23/2358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