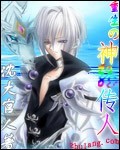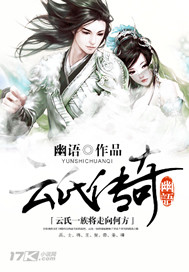平安传-第1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队缓缓地在稻田中间的大路上行进,马镫里的脚能感受到露水的凉意。天还没亮,但东边的天空已渐渐发白。在充满了相间气息的庄稼之间,骑枪竖立的黑影和盔甲金属摩擦的声音显得格格不入,好似在这大自然的景象中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冯友贤的内心也并没有因为宁静的凌晨而安宁,他的脑海里一遍遍地浮现出往事。作为一个武将,服从军令是基本,当时他未接到命令便不能擅自出击;等到进攻时,他也尽了自己的本份努力杀敌,无奈那时官军步军兵溃如山倒大量军队竟无法做出一点配合。冯友贤多次在心里认定,高都之战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渐渐蒙蒙亮了,各队马兵陆续穿过一片树林,对面有一个种着菜的山坡旱地,翻过山坡就应该是官军骑兵营的驻地了。
前面的斥候来报,许多官军骑兵已经离开营地、正在前面布阵。冯友贤却淡定地回应道:“官军扎营后极可能在南边的路上安插了暗哨,在我们行军时就察觉到了。这是情理之中,如果一支兵马在睡梦中被攻击倒是反常。不过他们刚得知有情况,必定准备不足,奇袭仍然是成功的。”
冯友贤随即策马爬上了坡顶,东边的微光和远处营地里的火光顿时驱散了山下的黯淡,战场就在眼前。从山坡菜地冲下去,距离官军营地还有大约一里的旷地,路边的庄稼地里大约种着一些豆类,并不影响骑兵横向展开。
远处传来了人马的喧嚣,据报官军正在营外列阵。冯友贤的脸色浮现出一丝嘲意:“马兵到了张忩手里也成了骑马的步军,他一受到袭击首先想到的就是列阵防御。”
越来越多的马冲上了山岗陆续集结,战马的头颅在晨光中展现出了昂首挺胸的气质,将士们纷纷眺望着前面的猎物。朱雀军这些马兵的骑术可能很多都比不上官军,除了一部分是从官军俘虏中征募的,很多是朱雀军内选拔的新丁:骑马倒是很容易学会,但骑马作战或许有点生疏。不过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冯友贤看来,马队不是一个个骑兵分开的,而是一个整体,重要的是斗志、信念和军纪。
战场的气息让他逐渐兴奋起来,作为一个武将,现在应该做的仅仅是是打败面前的敌人、很纯粹很简单的动机,没有军人愿意面对战败的耻辱。
整个骑兵团分四哨建制,前哨、后哨、左哨、右哨,称呼除了是个名称、也便于在扎营时分派地方,但不代表战阵上的位置。
冯友贤当即下了军令。自带前哨、后哨共约七百五十骑,以总旗为两排单位,对官军中央发动冲锋,意图直接洞穿撕开其阵营;左哨右哨分别机动到敌军两翼,集结之后,待中路进攻得逞,便从两翼冲锋,再度分割撕裂敌军阵型。
布置十分简单,冯友贤的命令十分明确,保持大队的冲击力,无须在中间缠斗,冲破之后,转身整顿继续冲击。
各哨千总得令后整顿了兵马。冯友贤喊了一声:“出发!”顿时一千多骑在山野间小跑起来,他们先从山坡上俯奔而下,马蹄声顿时隆隆作响,如同云间酝酿的雷鸣闪电。
无数的战马在身边奔腾,风声在耳边呼啸,朦胧的景色飞快地闪在身后。此时此刻冯友贤几乎忘却了内心的矛盾,他已经念头通达了。如同鸟儿在空中飞翔,鱼在水中畅游,只要一骑在马背上冲锋,他就感觉自己在飞翔,此生从未想象过不能骑马作战的人生是多么无趣。
闪电般击败敌手,其中的信念已经远远脱离了杀戮。并肩作战的兄弟、骑兵冲锋无法后退,同甘共苦的战马,马在冯友贤的心里不是牲口、而是骑兵团中的一员,值得信赖的伙伴。这种信赖和命运相系的感受,只有同样经历过的兄弟才能真正领会。
一百五十步,不需要命令,将士们已纷纷准备好了武器。冯友贤从马上拔出了细长的马刀,指向前方大喊道:“杀!”众军条件反射般地喊出了训练时的话“为了荣耀”,一些人也大喊万岁。人们的血已经沸腾了。
一百五十步、一个步军用弓箭抛射也不能达到的远处,骑兵团不到二十弹指间(二十秒)就冲到了官军跟前,几乎就是眼皮眨几下的工夫。同样大股骑兵冲锋,什么武艺之类的巧活几乎派不上用场,箭一般的速度飞驰而来,连来势都看不清楚。前锋马兵拿着丈余的骑枪,凭借这急速的冲击力,将钢铁的锋芒刺入了被动防御的官军马兵身上,盔甲完全挡不住如此锋芒。
骑枪直接洞穿了人的胸口,鲜血在风声中飞溅。说时迟那是快,冯友贤的两哨兵马如同炮弹击穿土墙一样,直接贯入官军阵营。前面丢掉骑枪的人拔出马刀,疯狂地劈砍。没有什么叮叮当当的拼杀,一触几乎是一刀毙命,冲锋的骑士躲不掉官军的攻击,官军也别想招架挥砍上来的刀锋。
人们没法停止,哪怕是身上的血在飙,只要没死就无法停下来。后面有多达三十余列的纵队在飞奔,一旦停下来只能被铁蹄践踏。
除了那叫人骨头生寒的金属刺入肉体的声音,还有砰砰砰的火器爆响,这回的枪响却全是官军发出的,只有官军骑兵才装备了三眼铳。血红的太阳升起时,旷野上的草木已经被血染红了。
第二百五十七章 责任(3)
府衙的二堂内,薛禄仍然用质疑的口气第二次问:“张忩的马队被击溃了?他在……那个地方叫……”旁边有个幕僚提醒道:“石场湾。”
这并不是因为薛禄玩忽职守,他是清楚自己手下骑兵位置的,只是昨晚驻扎的那地方实在是个太平凡的小地方,大部分人都没注意名字。如果不是张忩的骑兵部队多达三千多人在一夜之间在石场湾伤亡惨重崩溃如山倒,想来那地方可能永远也无法幸运地出现在府衙的官员口中。
于谦在一个早晨就仿佛疲惫了许多,他的脸色也看起来有点枯黄。此时令他心里难受的不仅是战败的消息,沉迷的气氛也叫人十分难受。突然损失了一大股马兵,官府里的人却一个个沉默少言。
于谦忽然有种感觉,地方上就如一滩死水一样,没有一点活力。府衙内陈旧的雕窗,红木椅子、以及上面四平八稳坐着的文官武将,都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大家一脸正然,个个都貌似很有城府,言行得体稳重,你很难从中找出一丝纰漏,可偏偏用起来就十分的不顺手。
大明帝国已经建国快有六十个年头了,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里,她仍然很年轻。但是自永乐时期以来,卫所军制已呈现固化趋势,各层上的将领就像这房间里的几把椅子,上面坐的总是那几个人,偶尔有人被群起排挤才会换上新的面孔。
这种莫名的感受让于谦也感觉到了一丝疲惫和厌倦。或许他自己也很所有人没多大的区别,他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坐姿比其它人还四平八稳,浑身一股官气,就算头发胡须花白的官吏也没人敢小视他的气度;而且走着同样的路子,科举谋出身,和朝廷重臣抱团,时刻观察着官场上的风向。年少时的一些梦想好像已经有几年没想起过了。
过了一会儿,于谦总算渐渐从这种低落的情绪中恢复过来。现实很简单:在大明朝,在智力天份等方面强于常人的人都愿意做官,这条路不仅能得到财富、更有社会地位和名声等等,总有一样是你想要的。
“以武阳侯之见,没有骑兵是不是就无法击退叛军了?”于谦慎重地问道。
薛禄皱眉道:“既无炮,又没了马兵,仅以步军对战恐怕极为不利。带过兵的人都知道,使用步军首重结阵,所以通常都是以破敌军之阵为要;下策双军交战,以杀伤敌方兵马迫使其无法承受伤亡而至丧失士气溃散,趁势掩杀。而今叛军步兵以犀利火器以待,百步内可穿铁甲,双军对垒,我们尚未接敌就坐实了下风,这等战法实难取胜。”
于谦微微点头赞同,他虽不是武将,但也想象得到战场上的情况。对于叛军火器百步穿甲的厉害,应该也是可信的。不仅薛禄、朱勇用实战证实了,连锦衣卫掌握的消息也是如此。
渐渐地总算有人开始提一些法子,有人说应该把主力撤进常德、武陵等城内,依托工事先行固守,再下令长沙增派马兵驰援;但是没有人敢拍着胸脯保证在几十门大炮的攻击下,城防能坚持到援兵到来,况且长沙又不是在场的官将们管的地盘,也无法保证他们是否能及时驰援;到了更难保证一定能击败叛军。
这个时代的战争动员速度很慢,特别是农耕国家。理论上湖广一省就能集结十万规模的军队,但是平时任何重镇都难以保持这么大规模的人数,多是分散在各卫所军田上甚至民间军户中,要聚集起来组成大军征发需要一定的时间。于巡抚和武阳侯都不是神仙,他们也没办法在几天之内就把一支军队弄到常德来增援,而且要打败拥有优势火力的敌军。
大伙表面上不断出谋划策,但形势因石场湾一战后已经更加恶劣。
议事无果而散,城外的炮声仍在络绎轰鸣,此时叫普通人望而生畏的六扇门也在炮声中颤抖了。于谦在离开府衙去往巡抚行馆的路上神情凝重。
他私下对随行的王俭说:“或许我们应该准备充分之后再和叛军开战,现在时机尚不成熟。常德府的一万多将士是湖广西部各府的主力,没有必要葬送在这个地方。”
王俭忙劝道:“学生观常德的官将都未失战心,若是不经决战就撤退,好像是咱们堂堂官军怕了一股叛贼,有损官军之威……说出去也不太好听。”
王俭在于谦面前自称学生,实则不是真的授业于他,只是一向追随出于尊敬的缘故。
于谦是明白王俭这番话的好心的,他并非真的怕失官军威名脸面,实则是为于谦考虑。本来丢城失地就是莫大的罪责,如果通过于谦来下令放弃一个府,而府里本来有多达一万余守军……这种事在朝廷官场上实在不好交代。索性这样,还不如守城战败的好,这样一来没守住天子的城池应该负责任的人就多了。
没守住城,巡抚作为节制一省军政要务的大吏虽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主管军务的总兵官薛禄也脱不了干系,甚至武昌三司的人也可以罚俸惩戒;还有常德府的知府,作为一府长官收住自己的辖地是最大的职责,难逃其咎。出了事如果巡抚心黑,完全可以找个替罪羊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朝里好像没靠山的赵知府。
于谦暂回行馆后,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头上坐了许久,他时而沉思,时而抬头叹息。王俭一直恭敬地站在他的旁边,寸步不离。
奴仆沏了一杯茶端上来,细看那杯盖边上有个缺。昨晚有个丫头不小心把茶杯磕碰了一下,当时忙着说要换新的来,但于谦说并不影响使用,叫丫头留下了。
良久之后,于谦终于镇定地对王俭说道:“你去告诉武阳侯,就说传我的命令,让他尽快准备,制定官军撤出常德的方略。”
王俭愣了愣,情知恩师已经下定了决心,却仍然忍不住再次提醒道:“真的要这么下令么?或许薛大人等都想要盖印的正式公文。”
于谦仰望无尽的天空,淡淡说道:“谁都知道,眼下最好的法子就是暂且撤退,为今后围剿时保留住这一万多战兵的实力,而不是无谓地葬送在这里。但是总有人要担这个责任,于某自问这点责任还是担得起的。若是他日有人要借此言语,那便由着别人说罢,我但求问心无愧。”
王俭听罢深深一鞠,满怀敬意地说:“学生遵命。”
很快薛禄、知府赵敏、将军覃有胜马岱等都赶来行馆见于谦了,他们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这帮人无论文武都不是傻子,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于谦是在主动为他们背黑锅。
人心都是肉长的,于谦实实在在地挡枪,一些武将心怀感激纷纷请求作为前锋先率军打一仗以观后效。但于谦决意已定,对众人淡淡说道:“本官身为湖广巡抚,所虑并仅是常德一地。湖广值多事之秋,为患者不只张宁之叛军。巡抚诸僚自有安排,各位将军只管遵从下令便是。”
众人只见于谦脸上面无表情,好似深藏玄机。不乏一两个人见状心里多想,猜测是不是武昌受到汉王的威胁了,所以湖广各地要尽量保存实力之类的。
这种情况下,于谦又坚持下令,大伙便爽快地答应了谋划大军撤出常德府。
不过他们刚刚出来,王俭就追上来了,向薛禄拜道:“方才侯爷等刚走,恩师就说了几句话,在下觉得应该说给侯爷听听。薛禄道:“王先生请说。”
“恩师言,大丈夫者,能屈能伸。世间懂得放弃的人少,知进退的人更少。”王俭道。
薛禄等人正在琢磨这句话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