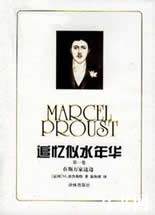出走十五年_余秋雨-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乡关何处》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一九九四年四月)
山居笔记·序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纔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数据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数据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纔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它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霜冷长河·序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
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纔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
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旋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纔稍稍有所收敛。
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
一次是长江。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NHK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坝,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懮伤。为何懮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懮伤。那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懮伤?正是这种懮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另一次是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懮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大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他们选了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象样。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时,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严寒而丧命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悲壮得令人神往。
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一个人坐在船舱顶篷上这么想着,又一个夜晚来到了。诗人李琦从甲板上伸头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构思什么,走开了。不久,见驾驶舱里有人在招呼,走近前去,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说:『我是船长,你这么坐着有危险,进这儿来吧。”
在驾驶舱互通姓名,船长居然与我同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