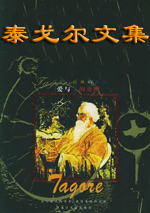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诗人抒情诗选_诺贝尔文学奖-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青青黄黄地亮着,四周镶着的五彩石上,
又雕刻着的海豚在愁惨的光中游泳。
那古旧的壁炉架上展现着一幅
犹如开窗所见的田野景物,
那是翡绿眉拉变了形,遭到了野蛮国王的
强暴:但是在那里那头夜莺
她那不容玷辱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沙漠,
她还在叫唤着,世界也还在追逐着,
“唧唧”唱给脏耳朵听。
其它那些时间的枯树根
在墙上留下了记认;凝视的人像
探出身来,斜倚着,使紧闭的房间一片静寂。
楼梯上有人在拖着脚步走。
在火光下,刷子下,她的头发
散成了火星似的小点子
亮成词句,然后又转而为野蛮的沉寂。
“今晚上我精神很坏。是的,坏。陪着我。
跟我说话。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啊。
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
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
我想我们是在老鼠窝里,
在那里死人连自己的尸骨都丢得精光。
“这是什么声音?”
风在门下面。
“这又是什么声音?风在干什么?”
没有,没有什么。
“你
“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
“不记得?”
我记得
那些珍珠是他的眼睛。
“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脑子里竟没有什么?”
可是
噢噢噢噢这莎士比希亚式的爵士音乐——
它是这样文静
这样聪明
“我现在该做些什么?我该做些什么?
我就照现在这样跑出去,走在街上
披散着头发,就这样。我们明天该作些什么?
我们究竟该作些什么?”
十点钟供开水。
如果下雨,四点钟来挂不进雨的汽车。
我们也要下一盘棋,
按住不知安息的眼睛,等着那一下敲门的声音。
丽儿的丈夫退伍的时候,我说——
我毫不含糊,我自己就对她说,
请快些,时间到了
埃尔伯特不久就要回来,你就打扮打扮吧。
他也要知道给你镶牙的钱
是怎么花的。他给的时候我也在。
把牙都拔了吧,丽儿,配一副好的,
他说,实在的,你那样子我真看不得。
我也看不得,我说,替可怜的埃尔伯特想一想,
他在军队里耽了四年,他想痛快痛快,
你不让他痛快,有的是别人,我说。
啊,是吗,她说。就是这么回事。我说。
那我就知道该感谢谁了,她说,向我瞪了一眼。
请快些,时间到了
你不愿意,那就听便吧,我说。
你没有可挑的,人家还能挑挑拣拣呢。
要是埃尔伯特跑掉了,可别怪我没说。
你真不害臊,我说,看上去这么老相。
(她还只三十一。)
没办法,她说,把脸拉得长长的,
是我吃的那药片,为打胎,她说。
(她已经有了五个。小乔治差点送了她的命。)
药店老板说不要??,可我再也不比从前了。
你真是个傻瓜,我说。
得了,埃尔伯特总是缠着你,结果就是如此,我说,
不要孩子你干吗结婚?
请快些,时间到了
说起来了,那天星期天埃尔伯特在家,他们吃滚烫的烧火腿,
他们叫我去吃饭,叫我乘热吃——
请快些,时间到了
请快些,时间到了
明儿见,毕尔。明儿见,璐。明儿见,梅。明儿见。
再见。明儿见,明儿见。
明天见,太太们,明天见,可爱的太太们,
明天见,明天见。
三、火诫
河上树木搭成的蓬帐已破坏:树叶留下的最后手指
想抓住什么,又沉落到潮湿的岸边去了。那风
吹过棕黄色的大地,没人听见。仙女们已经走了。
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
河上不再有空瓶子,加肉面包的薄纸,
绸手帕,硬的纸皮匣子,香烟头
或其他夏夜的证据。仙女们已经走了。
还有她们的朋友,最后几个城里老板们的后代;
走了,也没有留下地址。
在莱芒湖畔我坐下来饮泣……
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
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我说话的声音
不会大,也不会多。
可是在我身后的冷风里我听见
白骨碰白骨的声音,慝笑从耳旁传开去。
一头老鼠轻轻穿过草地
在岸上拖着它那粘湿的肚皮
而我却在某个冬夜,在一家煤气厂背后
在死水里垂钓
想到国王我那兄弟的沉舟
又想到在他之前的国王,我父亲的死亡。
白身躯赤裸裸地在低湿的地上,
白骨被抛在一个矮小而干燥的阁楼上,
只有老鼠脚在那里踢来踢去,年复一年。
但是在我背后我时常听见
喇叭和汽车的声音,将在
春天里,把薛维尼送到博尔特太太那里。
啊月亮照在博尔特太太
和她女儿身上是亮的
她们在苏打水里洗脚
啊这些孩子们的声音,在教堂里歌唱!
吱吱吱
唧唧唧唧唧唧
受到这样的强暴。
铁卢
并无实体的城
在冬日正午的黄雾下
尤吉尼地先生,哪个士麦那商人
还没光脸,袋里装满了葡萄干
到岸价格,伦敦:见票即付,
用粗俗的法语请我
在凯能街饭店吃午饭
然后在大都会度周末。
在那暮色苍茫的时刻,眼与背脊
从桌边向上抬时,这血肉制成的引擎在等侯
像一辆出租汽车颤抖而等候时,
我,帖瑞西士,虽然瞎了眼,在两次生命中颤动,
年老的男子却有布满皱纹的女性乳房,能在
暮色苍茫的时刻看见晚上一到都朝着
家的方向走去,水手从海上回到家,
打字员到喝茶的时候也回了家,打扫早点的残余,点燃了
她的炉子,拿出罐头食品。
窗外危险地晾着
她快要晒干的内衣,给太阳的残光抚摸着,
沙发上堆着(晚上是她的床)
袜子,拖鞋,小背心和用以束紧身的内衣。
我,帖瑞西士,年老的男子长着皱褶的乳房
看到了这段情节,预言了后来的一切——
我也在等待那盼望着的客人。
他,那长疙瘩的青年到了,
一个小公司的职员,一双色胆包天的眼,
一个下流家伙,蛮有把握,
正像一顶绸帽扣在一个布雷德福的百万富翁头上。
时机现在倒是合式,他猜对了,
饭已经吃完,她厌倦又疲乏,
试着抚摸抚摸她
虽说不受欢迎,也没受到责骂。
脸也红了,决心也下了,他立即进攻;
探险的双手没遇到阻碍;
他的虚荣心并不需要报答,
还欢迎这种漠然的神情。
(我,帖瑞西士,都早就忍受过了,
就在这张沙发或床上扮演过的;
我,那曾在底比斯的墙下坐过的
又曾在最卑微的死人中走过的。)
最后又送上形同施舍似的一吻,
他摸着去路,发现楼梯上没有灯……
她回头在镜子里照了一下,
没大意识到她那已经走了的情人;
她的头脑让一个半成形的思想经过:
“总算玩了事:完了就好。”
美丽的女人堕落的时候,又
在她的房里来回走,独自
她机械地用手抚平了头发,又随手
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片子。
“这音乐在水上悄悄从我身旁经过”
经过斯特兰德,直到女王维多利亚街。
啊,城啊城,我有时能听见
在泰晤士下街的一家酒店旁
那悦耳的曼陀铃的哀鸣
还有里面的碗盏声,人语声
是渔贩子到了中午在休息:那里
殉道堂的墙上还有
难以言传的伊沃宁的荣华,白的与金黄色的。
长河流汗
流油与焦油
船只漂泊
顺着来浪
红帆
大张
顺风而下,在沉重的桅杆上摇摆。
船只冲洗
漂流的巨木
流到格林威治河区
经过群犬岛。
weialalaleia
wallalaleialala
伊丽莎白和莱斯特
打着桨
船尾形成
一枚镶金的贝壳
红而金亮
活泼的波涛
使两岸起了细浪
西南风
带到下游
连续的钟声
白色的危塔
weialalaleia
wallalaleialala
“电车和堆满灰尘的树。
海勃里生了我。里其蒙和邱
毁了我。在里其蒙我举起双膝
仰卧在独木舟的船底。
“我的脚在摩尔该,我的心
在我的脚下。那件事后
他哭了。他答应‘重新做人’。
我不作声。我该怨恨什么呢?”
“在马该沙滩
我能够把
乌有和乌有联结在一起
脏手上的破碎指甲。
我们是伙下等人,从不指望
什么。”
啊呀看哪
于是我到迦太基来了
烧啊烧啊烧啊烧啊
主啊你把我救拔出来
主啊你救拔
烧啊
四、水里的死亡
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死了已两星期,
忘记了水鸥的鸣叫,深海的浪涛
利润与亏损。
海下一潮流
在悄声剔净他的骨。在他浮上又沉下时
他经历了他老年和青年的阶段
进入漩涡。
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啊你转着舵轮朝着风的方向看的,
回顾一下弗莱巴斯,他曾经是和你一样漂亮、高大的。
五、雷霆的话
火把把流汗的面庞照得通红以后
花园里是那寒霜般的沉寂以后
经过了岩石地带的悲痛以后
又是叫喊又是呼号
监狱宫殿和春雷的
回响在远山那边震荡
他当时是活着的现在是死了
我们曾经是活着的现在也快要死了
稍带一点耐心
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
岩石而没有水而有一条沙路
那路在上面山里绕行
是岩石堆成的山而没有水
若还有水我们就会停下来喝了
在岩石中间人不能停止或思想
汗是干的脚埋在沙土里
只要岩石中间有水
死了的山满口都是龋齿吐不出一滴水
这里的人既不能站也不能躺也不能坐
山上甚至连静默也不存在
只有枯干的雷没有雨
山上甚至连寂寞也不存在
只有绛红阴沉的脸在冷笑咆哮
在泥干缝猎的房屋的门里出现
只要有水
而没有岩石
若是有岩石
也有水
有水
有泉
岩石间有小水潭
若是只有水的响声
不是知了
和枯草同唱
而是水的声音在岩石上
那里有蜂雀类的画眉在松树间歌唱
点滴点滴滴滴滴
可是没有水
谁是那个总是走在你身旁的第三人?
我数的时候,只有你和我在一起
但是我朝前望那白颜色的路的时候
总有另外一个在你身旁走
悄悄地行进,裹着棕黄色的大衣,罩着头
我不知道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但是在你另一边的那一个是谁?
这是什么声音在高高的天上
是慈母悲伤的呢喃声
这些带头罩的人群是谁
在无边的平原上蜂拥而前,在裂开的土地上蹒跚而行
只给那扁平的水平线包围着
山的那边是哪一座城市
在紫色暮色中开裂、重建又爆炸
倾塌着的城楼
耶路撒冷雅典亚力山大
维也纳伦敦
并无实体的
一个女人紧紧拉直着她黑长的头发
在这些弦上弹拨出低声的音乐
长着孩子脸的蝙蝠在紫色的光里
嗖嗖地飞扑着翅膀
又把头
![[迪安·德尔文_罗朗·埃梅里希_斯蒂文·穆斯塔德_王荣生] 天煞--独立日烽火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