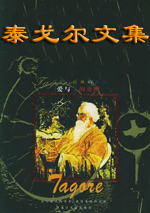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诗人抒情诗选_诺贝尔文学奖-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和平也没有土地,
只是一副骷髅,一只钟,人们在它之中去死。
我掀开碘的绷带;把双手伸向
杀死死亡的无穷痛苦;
在创伤里,我只逢到一阵寒风,
从心灵的模糊的隙缝里吹进。①
①以上五节,是诗人在登上马克丘·毕克丘之前,抒发对人民的苦难、暴力和贫困所造成的死亡,以及自己的不幸遭遇的悲忿之情。
vi
于是,我在茂密纠结的灌木林莽中,
攀登大地的梯级,
向你,马克丘·毕克丘,走去。
你是层层石块垒成的高城,
最后,为大地所没有掩藏于
沉睡祭服之下的东西所居住。
在你这里,仿佛两条平行的线,
闪电的摇篮和人类的摇篮,
在多刺的风中绞缠一起。
石块的母亲,兀鹰的泡沫。
人类曙光的崇高堤防。
遗忘于第一批砂土里的大铲。
这就是住所,这就是地点;
在这里,饱满的玉米粒,
升起又落下,仿佛红色的雹子。
在这里,骆马的金黄色纤维
给爱人,给坟墓,给母亲,给国王,
给祈祷,给武士,织成了衣服。
在这里,人的脚和鹰的脚
在一起歇息于险恶的高山洞穴,
以雷鸣的步子在黎明踩着稀薄的雾霭,
触摸着土地和石块,
直到在黑暗中或者死亡中把它们认识。
我瞧着衣服和手;
瞧着鸣响的洞穴里水的痕迹;
瞧着那被一张脸的接触所软化的墙,
它以我的眼睛望着大地上的灯,
它以我的手给消失的木材上油,
因为一切的一切:衣服,皮肤,杯子,
语言,美酒,面包,
都没有了,落进了泥土。
空气进来,以柠檬花的指头,
降到所有沉睡的人身上;
千年的空气,无数个月无数个周的空气,
蓝的风,铁的山岭的空气,
犹如一步步柔软的疾风,
磨亮了岩石孤寂的四周。
vii
独一的深渊里的死者,沉沦中的阴影,
那深沉的程度,
就如你们的庄严肃穆一样。
那真实的,那最炽烈的死亡来到了,
于是从千疮百孔的岩石,
从殷红色的柱头,
从逐级递升的水管,
你们倒下,好象在秋天,
好象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空旷的空气已经不再哭泣,
已经不再熟悉你们陶土的脚,
已经忘掉你们的那些大坛子,
过滤天空,让光的匕首刺穿;
壮实的大树被云朵吞没,
被疾风砍倒。
它顶住了一只突然压下的手,
来自高空,直至时间的终结。
你们不再是,蜘蛛的手,
脆弱的线,纠缠的织物;
你们失落的有多少:风俗和习惯,
古老的音节,光彩绚丽的面具。
但是,石块和语言坚定不变,
城市好象所有的人手里举起的杯子;
活人,死人,沉默的人,忍受着
那么多的死,就是一垛墙;那么多的生命
一下子成为石头的花瓣,永恒的紫色玫瑰,
就是这道冰冷殖民地的安第斯山大堤。
等到粘土色的手变成了粘土,
等到小小的眼睑闭拢,
充满了粗砺的围墙,塞满了堡垒,
等到所有的人都陷进他们的洞穴,
于是就只剩下这高耸的精确的建筑,
这人类曙光的崇高位置,
这充盈着静寂的最高的容器,
如此众多生命之后的一个石头的生命。①
①马克丘·毕克丘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文化,怎么会突然消灭,成为一座废墟,至今无法解释。
viii
跟我一起爬上去吧,亚美利加的爱。
跟我一起吻那秘密的石块。
乌罗邦巴①奔流的白银,
扬起花粉,飞进它黄色的杯子;
飞在藤蔓纠结的空隙里,
飞在石头的植物,坚硬的花环间,
飞在山间峡谷的静寂上。
来吧,微小的生命,来到泥土的
两翼之间,同时——晶莹而凛冽,
冲击着空气,劈开了顽强的绿玉,
狂暴的水啊,来自白雪的水。
爱情,爱情,即使在险恶的黑夜,
从安第斯敲响的燧石,
直至红色膝头的黎明,
都总在凝望这个白雪的盲目的儿子。
啊,白练轰响的维尔卡马约,②
在你雷鸣的水流破碎成为
白色的泡沫,仿佛受创的雪之时,
在你强劲的南风疾驰而下,
唱着闹着,吵醒了天空之时,
你这是带来的什么语言,
给予几乎刚从你安第斯泡沫脱出的耳朵?
是谁抓着寒冷的闪光,
锁住了留在高处,
在冰凌的泪珠中分割,
在飞快的剑光上鞭挞;
猛击坚强的花蕊,
引向武士的床头,
使岩石的终极大为惊慌?
你那被逐的火花说的是什么?
你那秘密的背叛的闪光
曾经带着语言到处旅行?
是谁,在打碎冰冻的音节,
黑色的语言,金黄的旗帜,
深沉的嘴巴,压抑的呼喊,
在你的纤弱的水的脉管里?
是谁,在割开那从大地上来看望的
花的眼皮?
是谁,抛下一串串的死者,
从你衰老的手里下降,
到地质的煤层中
收取他们已经得到的黑夜?
是谁,扔掉了纠结的树枝?
是谁,重新埋葬了告别的言辞?
爱情,爱情啊,别走到边沿,
别崇拜埋没的头颅;
让时间在泉源枯竭的大厅完成自己的塑像,
然后,在飞速的流水和高墙之间,
收集隘道中间的空气,
风的并列的平板,
山岭的乱冲横撞的河道,
露水的粗野的敬礼,
于是,向上攀登,在丛莽中,一朵花一朵花地,
踏着那条从高处盘旋而下的长蛇。
在山坡地带,石块和树丛,
绿色星星的粉末,明亮的森林,
曼图③在沸腾,仿佛一片活跃的湖,
仿佛默不作声的新的地层。
到我自己的生命中,到我的曙光中来吧,
直至崇高的孤独。
这个死的王国依然生存活跃。
这只大钟的钟面上,兀鹰的血影
象艘黑船那样划过。④
①乌罗邦巴,秘鲁的一条河流。
②维尔卡马约,秘鲁的一条河流。
③曼图,山谷名。
④诗人怀着对美洲的爱,向上攀登,俯视两条湍急的河流,一个深谷。
ix
星座的鹰,浓雾的葡萄。
丢失的棱堡,盲目的弯刀。
断裂的腰带,庄严的面包。
激流般的梯级,无边无际的眼睑。
三角形的短袄,石头的花粉。
花岗岩的灯,石头的面包。
矿石的蛇,石头的玫瑰。
埋葬的船,石头的泉。
月亮的马,石头的光。
平分昼夜的尺,石头的书。
阵阵风暴之中的鼓。
沉没时间的珊瑚。
把指头磨光的围墙。
使羽毛战斗的屋顶。
镜子的枝条,痛苦的基础。
乱草所倾覆的宝座。
凶残的利爪的制度。
依着斜坡的强劲南风。
绿松石的一动不动的瀑布。
沉睡者的祖传的钟。
被统治的雪的颈枷。
躺在自己塑像上的铁。
无可接近的封闭的风暴。
美洲豹的手,血腥的岩石。
帽样的塔,雪样的辩论。
在指头和树根上升起的黑夜。
雾霭的窗户,坚强的鸽子。
凄凉的植物,雷鸣的塑像。
基本的群山,海洋的屋顶。
迷途的老鹰的建筑。
天庭的弦,高空的蜜蜂。
血的水平线,构造的星星。
矿石的泡沫,石英的月亮。
安第斯的蛇,三叶草的额头。
寂静的圆顶,纯洁的祖国。
大海的新娘,教堂的树木。
盐的枝条,黑翅膀的樱桃。
雪的牙齿,寒冷的雷声。
爪一样的月亮,威胁的石块。
冰凉的发髻,空气的行动。
手的火山,阴暗的瀑布。
银的波浪,时间的方向。①
①以上以示马克丘·毕克丘的雄伟。
x
石块垒着石块;人啊,你在哪里?
空气接着空气;人啊,你在哪里?
时间连着时间;人啊,你在哪里?
难道你也是那没有结果的人的
破碎小块,是今天
街道上石级上那空虚的鹰,
是灵魂走向墓穴时
踩烂了的死去的秋天落叶?
那可怜的手和脚,那可怜的生命……
难道光明的日子在你身上
消散,仿佛雨
落到节日的旗帜上,
把它阴暗的食粮一瓣一瓣地
投进空洞的嘴巴?
饥饿,你是
人的合唱,你是秘密的植物,伐木者的根;
饥饿,你要把你这一带暗礁升高,
直至成为林立的巍峨的高塔?
我讯问你,道路上的盐,
把匙子显示给我看;建筑,
让我用一根小棍啃石块的蕊,
让我爬上所有的石级直至无所有,
让我抓着脏腑直至接触到人。
马克丘·毕克丘,是你把石块垒上石块,
而基础,却是破衣烂衫?
把煤层堆上煤层,而以眼泪填底?
把火烧上黄金,那上面还
颤动着大滴大滴鲜红的血?
把你埋葬下的奴隶还我!
从泥土里挖出穷人的硬面包,
给我看奴隶的衣服
以及他的窗户。
告诉我,他活着的时候怎么睡觉。
告诉我,他在梦中是否
打鼾,半张着嘴,仿佛由于疲劳
在墙壁上挖的一个黑坑。
墙啊,墙!他的梦是否被每一层石块
压着,是否与梦一起落到它下面,
如同落在月亮下面一样!
古老的亚美利加,沉没了的新娘,
你的手指,也从林莽中伸出,
指向神祗所在的虚无高空,
在光采华丽的婚礼旌旗之下,
掺杂在鼓与矛的雷鸣声中。
你的指头,也是,也是
玫瑰所抽发,寒流的线条,
是新谷的血红胸脯,
转变成为材料鲜艳的织物,坚硬的器皿,
被埋葬的亚美利加,你也是,也是在最底下,
在痛苦的脏腑,象鹰那样,仍然在饥饿?①
①马克丘·毕克丘的古老人民,也是被剥削者,受压迫者。
xi
让我的手伸进五光十色的光辉,
伸进石块的黑夜;
让遗忘了的古老的心,
象只千年被囚的鸟,在我身上搏动!
让我现在忘掉这幸福,它比海还宽,
因为人就是比海及其岛屿更宽;
应该落入其中如同下井,再从底层脱出,
借助于秘密的水和埋没的真理的枝条。
让我忘掉吧,宽阔的石板,强大的体积,
普遍的尺度,蜂房的基石;
让我的手现在从曲尺滑到
粗糙的血和粗糙的衣服的斜边上。
忿怒的兀鹰,在飞行中,
仿佛红鞘翅甲虫的蹄铁,猛撞我的额头。
那杀气的羽毛的疾风,扫起
倾斜的石级上乌沉的尘土。
我看不见这只疾飞的飞禽,看不见它利爪的钩,
我只看见古老的人,被奴役的人,在田野里睡着的人。
我看见一个身体,一千个身体,一个男人,一千个女人,
在雨和夜的昏沉乌黑的疾风之中,
与雕像的沉重石块在一起:
石匠的胡安,维拉柯却①的儿子,
受寒的胡安,碧绿星辰的儿子,
赤脚的胡安,绿松石岩的孙子,
兄弟,跟我一起攀登而诞生吧。
①胡安,代表普通的人。维拉柯却,秘鲁的第八世印加,1379—1430年在位。
xii
兄弟,跟我一起攀登而诞生。
给我手,从你那
痛苦遍地的深沉区域。
别回到岩石的底层,
![[迪安·德尔文_罗朗·埃梅里希_斯蒂文·穆斯塔德_王荣生] 天煞--独立日烽火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