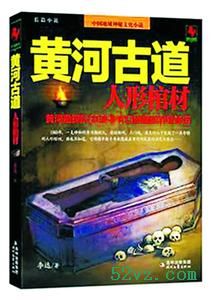雪落黄河静无声_从维熙-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范汉儒两眼直了:“她怎么还有这样的童心呢?真怪!”
“一点不怪。”我说:“我估摸这是给你的一封信。”
他将信将疑地,把这“纸船”拆开,几张白纸的背面,果然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汉儒同志:
现在我可以这么称呼你了,因为我已满了刑期,按规定可以算是半个公民了。
我很自卑,在你面前尤其自卑。虽然我在“女号”,离你们有几十里地远,但你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很多。田队长是个很有修养的劳改干部,她在对我们进行教育时,经常举出你在鸡场的事例,于是我了解了你。至于田队长对你怎么这样了解,我不好过问。据她说,在度荒年代,你宁可煮菜帮子吃,也不动农场一个鸡蛋。只凭这一点,就看出你是一个毅力极强的人。我们这些女囚,按说比男人更该自重,不,在那几年,她们无所不吃,在葡萄园干活时,把没成熟的酸葡萄往嘴里填;甚至刚刚打过农药的青桃,她们也在所不惜。我是狱医,经常为抢救这些因饥荒而丧失理性的女号,白天黑夜地奔忙。田队长还告诉我们:你清白如水,从鼠洞里掏出的四个鸡蛋都交公。
老实说,在这社会的最底层,我听见这些事倩,就象听童话那么新奇。按物理学解释:“一旦物质承受了超负荷的压力,没有不破碎或变形的。你是属于哪一种稀有物质呢——我常常这么想。记得,有一次你在总场部做养鸡方面的报告,我们 “女号”派代表去参加。那是我一次看到你。当时正是盛夏,你赤着双脚,头戴一顶荷叶形草帽,大概因为天气太热之故,你把草帽摘下来当扇子扇风,我才看见你面型特征。你前额是那么大,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电影中的列宁。
当然,这样的比喻很不恰当,可那是我的真实感觉,我找不出更好的比喻来了,只好这样吧!
“我……我不能再看了,这是给你一个人写的!”我尴尬地把眼神从信纸上收回来。
范汉儒用戴铐的手拉住了我:“刚才你分担了我的痛苦,现在,你有资格和我同享快乐。”
“信上快要出现……出现热乎词儿了,还是你一个人……”我站起身来。
“老弟!你是过来人了,当参谋就当到底嘛!你得帮我多拿主意呀!”
我只好又坐了下来。
范汉儒继续轻声读了下去。
后来,你来我们“女号”的养鸡场了,我很激动,似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流露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我用心里的尺,量了量我自己,我们中间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而这些距离,是座山,难以攀越;是条急流,有船也难以渡过。偏偏这时候,你在荒芜的古道旁向我开口了。我的心乱极了,真的,到今天我都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你的了;我的心一个劲跳,一直跳到我们分手……
还记得那次稻田风波吗?你们那位队长训斥你,我听了比训斥我还难受。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你产生了……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突然站起来,干了那么一手活儿。那天,我们“女号”冒雨收工回来,我刚换上干净衣裳,田队长就推开医务室的门,走了进来。她问我:“陶莹莹!那草里的苗真是你拔下来的吗?” 我很犹豫,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地来询问这件事情。我想说谎瞒她,但是她那双眼睛是诚挚的(她一直对我非常关心),我立刻把谎话咽了下去,把真话吐了出来:“不,不是。”“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拔的?”她问。我说:“田队长!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只觉得那么一个人,不该挨训。我……我太冒失了,今后决不再重犯这样的过失了,您批评吧。!”我低着头,等着她的批评;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我一抬头,不知她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医务室。真奇怪!
我一直惶惶不安。直等到我解刑的那天,她才告诉我,她不谴责我那次冒失行为;正相反,她认为我还没有丧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良知——尽管我当时是服刑的女囚!我影影绰绰从她嘴里知道,你们那位队长所以被撤了职,去当管理员,是她到场部告状的结果。几天前,她又把我找到队部办公室,我等着她布置任务,可她一直也没说话。
我问:“田队长!您有事吗?”
“没事,你走吧!”
我刚走出屋子,她又喊我:
“你回来!”
我重新站在她的办公桌前:“您今天是怎么了?”
“再过几天,你可能要离开你服过刑的土地了!”她声音极轻。
“去哪儿?”我马上说,“我不愿意走,我在这个队呆熟了。几年来,您对我帮助很大!”
“这不是经过人为的努力,就能把你留下来的事情。”她脸上露出忧郁的神色, “临走前,你有什么话说吗?”
我难过地说:“感谢您多年对我的教育,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听的不是这个。”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想法,比如:个人的生活问题,你还是个姑娘啊!”
“我没想法,只想一个人自食其力……”
“陶莹莹,这不是实话吧!在稻田发生的那件事,我这个当队长的可不是瞎子……”
我心乱如麻:“田队长,我……”
“你很有眼力,分得清黄土和朱砂。”她思忖地笑了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爱人在他们男队当队长,你如果真对他……在你临去山西之前,我可以通过我爱人对范汉儒透个信儿,范汉儒是个诚实的人……当然,范汉儒能不能原谅你犯过的那次错误我不敢担保,……你看,我这个当队长的,竟管起你的私事来了!”
“我……我……我……”我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这是你的自由,我只是问问你。”她解释着,“因为他们也去山西,山西有二十多个劳改点,不知把你们分到什么地方去。当然能到一块更好,万一要是离得很远,就难再有碰面的时候了,所以,我事先问问你。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心跳得挨着了嗓子眼,“田队长!我非常感谢您。我的父母都和我断绝了关系,您……”
“回去考虑一下,明后天给我个回话!记住,这是属于你的自由,不要因为我是队长,就有所屈从,我们今天谈话完全是平等的关系。”
我回到就业人员的宿舍,当天夜里失眠了!汉儒同志,我不是考虑我愿意不愿意,而是考虑到我不该和你建立那种关系。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而你虽是“右派”,品质却是水样的透明……
还没容我去回答田队长,开往山西的日期提前了。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匆匆忙忙地上了卡车,又匆匆忙忙地登上了火车。我的天!跟我们同车来山西的竟是你们那位队长!我的心真是不寒而栗!还算好,他没有认出我就是在稻田里干扰他对你发威的女犯!由于我是个“医生”缘故,被安排在九号车厢,这儿是押送人员专列,不象其它车厢那样拥挤。趁着还没有病号来找我的时刻,伏在小桌上给你写了这封信。因列车不停地摆动,字写得歪歪扭扭,请你原谅。我想写完信后,借着在车厢巡诊的机会递交给你。可是我不敢保证我自己,能有那么大的勇气——因为理智始终在我耳边回响: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我感情上已经不能自我克制,只好孤注一掷,听从上帝的安排了!
此祝 冬安
陶莹莹,于九号车厢
如果命运使我们一个天南,一个地北,也请你想办法回我一封信,因为我们女队的去处,总是可以打听到的。我等着!我期待着!
——陶莹莹又及
…………
我俩久久相对无言,围拢在我们周围的伙伴都肃然无声。人,在最激动的时刻,常常出现沉默,而现在,车厢里就沉浸在这种沉默之中。片刻之后,喧嚷声突然在车厢中迸发:“‘六点钟’,你真是个福神!”
“她就象她的名字一样透明!”
“这件衣裳是她有意留给你的!”
“这真是沙漠中的青草,苦难大地上的抒情诗!”
“祝福你!倒霉的范汉儒!”
“愿你们将来能百事如意!”
“……”
范汉儒用戴着手铐的双手,笨拙地叠着那几张信纸,他想把它仍然叠成一只船,但颤颤嗦嗦的手指怎么也不听他的指挥。我拿过来,沿着信纸上留下的折纹,把它叠成了原来的模样——一艘鼓着帆的小船。
他把它捧在手上,凝神地望着,望着。
我不想打扰他的思绪,闭上了眼睛。
“叶涛!别睡觉。窗外有条河!”他说。
“那是汾河!”我闭着眼睛回答。
“它流向哪里?”
“陪伴着咱们这趟车一直流向黄河!”
“要是把这只船放进河里……”
“老兄!你看不见河床已经开始封冻了吗?”
“那么说,它飘流不到它的终点了?”
“哪儿是它的终点?这儿——”我睁开眼睛指着他的心窝说,“这才是它的归宿!”
“不,它应该流进黄河。那儿浩浩荡荡,一泻千里,这张帆应当和我们编成一个开拓新生活的船队。黄河是我们伟大民族的诞生摇篮,你、我、她都应当无愧于我们光荣的祖先。”他神色异常激动,镜片后的两眼熠熠放光,“叶涛!刚才‘催命三郎’不是无意地露了一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什么河滨农场吗?从‘河滨”两个字上去分析,那儿一定靠近黄河。”
雪落黄河静无声九
“有可能。”
“不是可能,是一定。”
“一定。”我心酸地望着手铐下晃动着的铁锁。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将站在黄河之滨,对我的古老祖先说——我是古老黄河的子孙。”说着,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弯腰拾起被他抖落在地板上的呢大衣、重新给他披上,把他强接在座位上。并把这封叠成船形的信,从他手里拿过来装进呢大衣的衣兜——因为隔着车门玻璃,我看见崔队长已经点名归来,这是他返回干部车厢的必经之途。这个可气的呆子,显然不知道我的用意,还用两只手死死地捏着那只“船”。似乎还想再端详一会儿。我低声向他喊着:“拿给我!快——”
晚了。
崔队长已经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范汉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会有什么风险,他两眼依然望着那只“船”。在他看来,改造“右派”的政策条文上,并没有规定“右派”只能独身生活。因而这封信即使被崔队长抄走,也构不成什么问题。何况这一车厢里装的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呢?“摘帽右派”应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可是我的心跳得象一面鼓,因为这封信里不但涉及陶莹莹,更重要的是涉及受人尊敬的田队长;这位正走红运的左斜眼,是不难用这封信对“黑姚期”夫妇下蛆的。山西——渤海湾虽然云水迢迢,但他只要给那边胳膊上戴“红箍”的一封函件,说他们同情犯罪分子,就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再从范汉儒手里索取这只“船”了,以避免招起崔总指挥的怀疑,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儿静待命运的审判。
崔队长一手就把范汉儒手里那只船夺了过去,他用眼角睨着他说:“刚才我对你说啥子话来?叫你老老实实反省错误!你干啥子事情,戴着手铐还叠纸船玩!真是反动透顶,甘心当花岗石,去见上帝唆!”
“崔队长!这个纸船是我叠的。”我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了范汉儒,生怕他再惹出什么风波,“您想,他戴着手铐能叠这玩艺吗?我不该影响他集中精力反省罪行!您……您把它还给我吧!”我屏住气,两眼盯着那只“船”,生怕他突然把它打开,那就等于我引火自焚了。
“留着这东西干啥子用?嗯?”他抖擞着总指挥的威风,双手用力一绞,就把几层纸叠的“船”撕成碎片,往车厢角一抛,双手叉腰训!斥我们说,“你们应该对范汉儒展开积极的斗争么!范汉杰的亲弟弟,一窝儿反革命!要是放在社会上,早该送他上火葬场了!他还不感激文化大革命的恩德,还有心玩……玩啥子纸船。你要坐船上哪儿去?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别做那个梦了!等着你的是严管队……” 他说尽了革命词汇,又抖尽了威风,直到他说得口干舌焦,才披着棉大衣风风火火地走了。
阿弥陀佛!范汉儒在这次挨训的过程中,一声没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