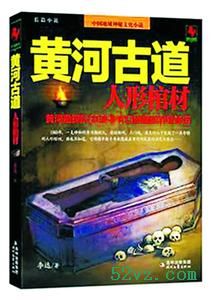雪落黄河静无声_从维熙-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室外,月光似水,遍地银白。这天的月亮实在太圆了,太亮了,以致使我几次抬头,都难以寻觅到一颗星斗。我知道,这是皎月之辉,湮没了满天星光的缘故。如果把我们这一百多人,都撒在天上变成星星的话,我们所有光源的总和,似也比不过范汉儒,他——不正是我们中间的月亮吗?为了延续生命,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无所不吃,公和私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青苹果、酸葡萄,甚至连水田里长着的稻穗都被他们用鞋底搓掉外壳。囫轮吞枣地填进肚子。为了挺过饥荒,这些万物之灵已经向类人猿“返祖”了。而范汉儒守着“聚宝盆”,却没丧失节操,他瘦得虽然如同一摇三晃的竹竿,公和私仍然泾渭分明,我不能不钦佩他的铮铮风骨。
我们坐在一根倒树上。我说:
“是不是队长对你开了天窗?有什么好消息?”
“老弟,别异想天开了。你没见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叫喊,要‘加强阶级斗争’ 吗?!丢掉幻想,作长期劳改的思想准备吧!”
“报丧,干吗半夜把我叫出来?”我快快不快地说。
“当然有喜事啦!”他两片厚嘴唇向上一翘,露出常见的喜劲儿,“精神营养虽然重要,但绝不万能!要想活得健康,归根到底还得靠物质营养。瞧瞧这个……” 他把一个手巾包摊在我面前,是一堆鸡蛋。
可借,我当时没带镜子,如果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模样的话,两只眼睛瞪得不会比地上的鸡蛋小多少。我看了半天才惊异地问:“哪儿来的?”
“你不是在队前看见了吗?”
“给了你四个……”我数了数,“现在是十四个呀!”
“这十个也是他给的呀!”
我审视地望着他:“是不是你学会了三只手?”
“老弟,你怎么这样看我范汉儒?我……”
“六点钟”有点动感情了,他摘下眼镜,直溜溜地瞪着我说,“这十个鸡蛋是他家里的母鸡下的,散会以后,他回家特意给我拿来,叫我把这十四个鸡蛋吃了,补补搓板一样的身子。”
我相信范仅儒的诚实,但是难以理解“黑姚期”的行动。诚然,在队列前向 “右派”坦率地检查他作风粗鲁,已经表现了他超越一般劳改干部的水平;但一个负责改造人的队长,自己肚子还“咕噜噜”叫,却主动拿出也许连自己孩子都舍不得吃的东西,给一个专政对象,则还是罕见的新闻。
“你不相信?”
“仅仅是不太理解。”
“你看,这是他的手巾,上边还印着‘公安’字样呢?”他把鸡蛋抖落在地下,又把手巾展开在我的眼前,“老弟!社会是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过去你是个写书的,应当比我理解得更清楚。人是有情物嘛!要是照你这个逻辑推理,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不早就被打入阴曹地府了吗?可是它一直流传着,你还对我称赞过这部小说哩!”
“那个典型环境和这儿不一样!”我争辩着。
“正因为不一样,‘黑姚期’的品质才显得更可贵。”范汉儒对着我耳朵高声说,“我本来死活不接他这兜鸡蛋,他对我发火了,嚷道:‘你是不是嫌太少?这是两只母鸡一个星期下的蛋。我没给孩子,没给老婆,给你拿来是看你还有中国人的骨头:将来政策松动一点,你还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这不是给你解馋的,是为了你能活着出去,懂吗?’叶涛,不知为什么,我鼻子发酸,‘吧嗒吧嗒’地掉下泪来……”
我沉默了。
他也若有所思。
“将来如果我还能拿笔,我一定不漏下这个‘黑姚期’,这个人物可很有嚼头……” 我对着一轮明月,内心十分感慨。
“能忘了我吗?”他指着自己的脑门。
“忘不了。”我笑了,“但你这‘六点钟’可是个反面典型,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后代人挖出你这具‘木乃伊’来,‘可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怪话要讲,活还得干。”他磕开一个煮熟的鸡蛋递给我,“无论怎么说咱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别说这些抽象的东西了,吃!吃了就能活下去。‘二一添作五’,咱俩一人七个。”
“单数不吉利。”我推给他一个鸡蛋。
他反而滚过来两个鸡蛋。
我把这两个鸡蛋又推了回去:“你是‘鸡倌’,理应你多吃两个。”
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用手指叩打着大脑门说:“对了!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正好是我的生日。让我们这两只属公鸡的,永远记住今天头上的月亮,永远记住在劳改队的这次夜宴吧!”
这,就是范汉儒把一根羽毛,卷在信笺之内的寓意所在……
有两性生存的地方就有爱情。“大劳改”和“二劳改”的罗曼史就是
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始的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保定早已被甩在后边……
石家庄又风驰而过……
列车闯出了长长隧洞……
列车开进了高山峡谷……
雪落黄河静无声二
我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充满了零乱的遐想。瞧!列车留下的烟和云拥抱了,它们很快在大自然里融为一体。按道理讲,生命元素相同的物质,都是会合二为一的:烟和云!云和霞!霞和气!气和水!水和烟……以此类推,周而复始。但是为什么范汉儒和陶莹莹却违反了这一自然法则呢?他和她的分子排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他俩在苦难中萌发了爱,象天上的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一样苦等,三中全会已经为他和她搭了鹊桥了呀!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反而来信向我告急呢?怪事!
“十四个鸡蛋的夜宴”之后,约摸过了三、四个年头——我们虚弱的身体已经复原时,“六点钟”结识了陶莹莹。“事不如意常八九”,偏偏在我们的扇面胸膛增加肌肉的时刻,我们失去了最可贵的东西——“黑姚期”调离了这支劳改队。接替“黑姚期”队长职务的,是个部队复员下来的班长。他姓崔,是个四川人,白净脸,淡眉毛。这个满口“啥子啥子”的白面书生,既没有“黑姚期”的热诚,也没有“黑姚期”的直率。他总用眼角瞟着我们,似乎这儿的一个个“右派”,都是一得到机会就会演“火烧草料场”的林冲。如果有人对他的训话做一个统计的话,他嘴边带出多少家乡方言“啥子”来,就会有多少“反革命”和“啥子”作伴:“你们是啥子东西?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是啥子右派?是‘反革命’右派!你们是啥子地方来的都有,不管是啥子地方来的,都是地地道道不掺假的‘反革命’。 ‘反革命’该干啥子活儿?下水塘耙地种谷。是啥子人叫你于养鸡的活儿?‘反革命’养的鸡,下的蛋都有‘反革命’味儿。从今天起,你……你……叫啥子姓名来着?对!对!你叫范汉儒……从今天起,你就别给我养啥子鸡了!那些鸡叫不是 ‘反革命’的刑事犯去养。”
完了。
在劳改农场闻名遐迩的范汉儒,莫名其妙地被摘去了“鸡倌”的乌纱帽。他去鸡房搬行李时,这位姓崔的“啥子”队长,象范汉儒的贴身马弁一样,紧紧地跟随他形影不离。本来,“六点钟”知趣一点,夹起行李就走也就完了;可范仅儒是个 “犟种”,告别鸡舍之前,偏要去看看那些“来亨”、“澳州黑”和“芦花翅”。范汉儒惜别似地招呼它们:
“‘大黑’!飞过来!”
“‘二黄’,来,让我最后看一眼。”
“‘花姑’!我要走了,我们换了队长,你们也要换爹娘了!”
“你这是讲的啥子话哟?”被“右派”们很快授予“催命三郎”绰号的崔队长,心中早已不耐烦了。此时,他那个嗅觉灵敏的鼻子,似乎从“六点钟”和鸡舍的诀别词中,闻出了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扬起双臂,把围绕在范汉儒身旁的鸡群轰开,朝范汉儒嚷道,“你是不是对调你去水田不满意?”
“满意。”范汉儒说,“我只想向崔队长提一个问题。你不叫我养鸡了,我是磨盘上的驴——听吆喝的,只是你说我养的鸡下的蛋都‘反革命’味儿,这可是违反遗传科学的。按队长你的说法,调个盗窃犯来养鸡,下了蛋是不是也会有股子贼腥味儿?”
“你反动——
“你是‘反革命’——
“你是加双料的‘反革命’!”
“催命三郎”讲不出个道道来,但政治帽子却非常富有。他一连给范汉儒戴上了一摞帽子还不算,还在全体大会上,号召所有成员加强对他的监督。范汉儒—— 这个被“黑姚期”看成鸡群中凤凰的人,在“催命三郎”眼里成了一只秃尾巴鸡了。
我们都为此愤愤不平:几年来,范汉儒为研究养鸡,付出了一腔热血;他为农场贡献了数以万计的鸡蛋,可是他自己的收获却是个零。全场各队谁不知有个大脑门的鸡倌?他顶风冒雨去各个队传授养鸡经验。就连男号从来不许涉足的女队,范汉儒也常来常往。“黑姚期”信任他,给他恢复了一个人所具有的全部智能。而这位“啥子”队长一来,范汉儒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催命三郎”那只“左视眼”,发出如同新式武器中的激光,一下把范汉儒的存在和他创造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六点钟’,别难过了。”晚上收工回来,躺在人挨人的大炕上,我安慰他说,“天有阴晴,月有圆缺,碰上这种东西,算咱们倒霉!”
他两眼看着房顶。一动不动。
“怎么了?你把荣誉看得那么重?”
他还是若有所失地圆睁着两只眼睛。
“你小子那点豁达劲儿跑哪儿去啦?”我捅了他一拳。
“唉!”范汉儒长吁一口气,“我该怎么对你说呢!养了几年鸡,我当然眷恋鸡房。可是你不知道,还有比那些长翅膀的,更值得我眷恋的东西。这些事情我都没对你说。”
“我知道,你想‘黑姚期’。”
“全队都想。不是这件事。”他摇摇头。
“这么说……是你独家独想的了?”
“对了。”
“我猜着了,二八月猫闹春,你大概是想起反‘右’前,爱你的女性函数了吧?”
他不安地蠕动了一下身子,舔舔厚厚的嘴唇,苦笑着说:“你瞧我这副模样,是姑娘追求的目标吗?不过,你猜的已经贴边了……不,还得说是个未知数。”
“那么说,你是有目标的了?”
“象一团雾。”他马上修正,“不,比雾还模糊。”
“你跟我打什么哑谜?”我用胳膊支撑起身子,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的脸, “忘了我们属鸡的同庚——”
“嘘——”他一下把我拉平了。
崔队长来查夜了。过去,“黑姚期”来查夜时,人们对他毫无防范;看书的,写字的,各随各便。崔队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没收所有成员的书。不管是文艺小说,还是理工医学都一概照收不误,而且一律不给收条。现在,这群落难秀才的宿舍,已经没有带铅字的纸片了。他还常常在夜里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用眼角那点斜光,打量着每一个没有睡去的成员。现在,他那锐利的目光,一下盯在了范汉儒的脸上。他走到我们的炕沿前狐疑地说:“你们说啥子话哩?为啥子见我来又不说了?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在对叶涛发泄你被调离鸡房的不满!”
我不愿他在我们眼前久留,应付地说:“没有。他没下过水田,分不清稻苗和稗草,正问我稻草和稗草的形状差别哩!队长,明天我们是不是去最边缘的那块水田拔草?”
我转移他注意力的提问,产生了效力,他下着命令:“明天开展稻田拔草竟赛,中午地头送饭,吃了饭连轴干,啥子龙门阵也别摆了,快快睡觉。”
他走后,我们继续刚才中断了的谈话,“六点钟”这才向我交代隐藏在他心中的秘密。
“该怎么对你说呐!也许有人生存的地方,就会产生爱情。你看,我们的祖先原始人,茹毛饮血,围树皮,住岩洞;生活比我们现代人不知要艰苦多少倍。可是他们并不因环境的极其艰苦而停止繁衍后代。”范汉儒摆开“龙门阵”,开始陈述他刚刚开篇的罗曼史,“我真想不到,在这个荒芜的地方,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话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奉‘黑姚期’之命,去一支女劳改队帮助女号鸡舍控制鸡瘟蔓延。她们监舍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