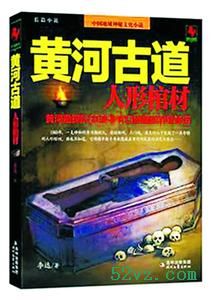雪落黄河静无声_从维熙-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河边散步。你知道,我所以留在这风沙小镇,一个是因为她,一个是我喜欢黄河。有一天,我实在压抑不住忧郁之情了,问她:‘你,为什么不和我去看黄河?’
“她摇摇头:‘我……我怕水。’”
“稻田拔草,你不是站在水里吗?”
“那水太浅了、刚淹没脚背。”
“咱们只是去散散步。又不是到黄河里去游泳?!”
“她连连摇头:‘不,不去。在这间小屋多安静!我们就这样对面坐着;你也别去!啊?’她的眼里流露出怯懦的光,真使人难以理解。”
“我依了她。我又给她讲我爸爸被日本人抓去,在黄河背纤的经历。她流露出不安的神色,用手捂着我的嘴说:‘老范!我求求你,不要讲这些了,你爸爸和你都是优秀的黄河子孙。我……怕听这样的故事,因为……’
“‘这为什么?’”我觉得她无意间泄露了一点心声。
“因为……你别问了,好吗?”
“我偏要问!”我来了犟劲,“难道你不是我们黄河儿女?”
她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她哭了,“你偏要追求我。我是……我是很喜欢你的,但终究……你不会喜欢我的,所以,我始终……始终没存奢望能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麻,一边给她擦泪,一边握住了她那颤抖的手,安慰她说: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我们在苦难的土地上相逢……”
“苦难中播下的种子,未必都能结果!”她痴呆呆地望着墙角说,“我何尝不想有个家,永远和你在一起!可是,理智早就告诉我这是一朵虚幻的花。我还是经受不住感槽的煎熬,从砖厂到这儿来了——这是我的过失!”她默默地垂下了头。
“莹莹!”
她看看我没有回音。
“莹莹!”我再次呼喊她。
她站起来,用我的手巾擦着脸上的泪痕。
“莹莹!”我第三次用生命呼喊她了,“你今天怎么了?”
她对着我桌子上那块破镜子,拍打一下自己零乱的头发,围上那块鸭黄头巾,淡淡地对我说:“老范!我们都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让我们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我在门口挡住她。
她心情矛盾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一直痴呆地看着我。她的目光专注而深邃,就好象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一样;然后,她突然紧紧地拥抱了我,吻我的前额,吻我的脸颊,吻我的嘴唇……同时,在我耳边喃喃地说:“原谅我吧!一个不配爱你的人,一个不值得你爱的人,打扰了你这么多年的平静!现在,我不能……不能…… 再瞒住你了。我……”
我们面对面地站着,连彼此的喘息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莹莹!你刚才说些什么?”我问。
“没说什么!”她低垂着头,胸膛起伏。
“你不是说有什么瞒住我的事吗?”我头脑开始清醒了,索性一竿子插到底。
“你最好不要听!”
“为什么?”
“因为截止到现在,陶莹莹的形象在你面前还是完美的,尽管脸上有了皱纹!我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个形象。不然……不然……”她眼角潮湿了,“你会后悔的!你会恨我的!”
我猜测地说:“你不是错划右派后,又犯有医疗事故而判刑的?”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反问我说:“如果我因为流氓犯罪……”
“只要是改了,我不计较!”我说。
“如果我曾经是个小偷呢?”
“只要是改了,我也不计较!”我重复地说。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它对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她不能有一次不忠。莹莹,你你……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我……我就是一个叛国犯!”她抬起了头,脸白得象一张纸。她嘴唇哆嗦着,不,连脸上的肌肉都抽搐起来了,“我早就想告诉你这一点,但我总怕因此而失去我已经获得了的东西;今天,我应该把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交给你了。”
我如受雷击,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她哇地一声哭了,从我屋里跑了出去。
我追出院子,喊着:“陶莹莹!你站一下!”
她听见我的喊声,反而跑得更快了。
“你在骗我,这绝不会是真的!”我似乎是疯了。
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跑向了河滨小站。
小站上熙熙攘攘,人和人接踵擦肩。那些旅客可能真地把我当成了疯子,互相交头接耳;认识我的学生,则把我围拢起来:
“范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您准备乘火车到哪儿去?”
“是啊!我是准备到哪儿去呀?”我昏热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如果她真是…… 我该怎么办?”我沮丧地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垂下了头。我希望陶莹莹坦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将承受信念和爱情的严酷折磨,它就象两个人在我心上拉着一把大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经得起心河滴血的痛苦。
“我认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基于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没有沉沦。难道在冰河解冻,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反而把我视若生命的东西丢开吗?我没有别的幻想了,唯一的冀求,是保存着陶莹莹昔日留给我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曾经背叛过祖国的人!不,这不是冀求了,而是对命运的虔诚析祷。为此,我特意去找了政委兼场长的姜老头,但是我的希望破灭了,姜老头告诉我,陶莹莹确实有过逃离祖国的行为。她不是什么小偷、流氓犯,五七年她被错划右派后,并没有出过什么医疗事故,而是和另一个医生一起从国境叛逃。她的同伙,游过了国境河,她游到河心,被边防军抓获。叶涛!我如同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在这风沙小镇上又没法跟人说,所以给你发了一封急信……”
我沉默地低下头,说不出一句话。他手指夹着那支早已熄灭的烟蒂,竟忘了把它抛进烟缸。
火车奔驰着,奔驰着……
列车员又在播送着《黄河大合唱》了。
“后来呢?”我自感声音里充满苦涩。
“姜场长让我自己抉择。”
“你怎么打算?”
“你是了解我的,尽管我们历尽沧桑,却没做过一件有损于国家的事情。我常想:屈原受了那么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楚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汩罗江,被后代称之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么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么能再继续下去?— —虽然,这对我比刀剜心还疼,对她来说如同失去生命;但随着岁月的更迭,也许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范汉儒摘下那副眼镜,下意识地擦来擦去,“我把你叫来,是倾吐一下我心中的苦水,听听你的意见。“
“陶莹莹经受得住这个致命打击吗?”我忧心忡忡地问。
“别看她外表懦弱,她是个很坚强的人。我们是一度同路的朋友,将来也想保持这种关系。
“她不一定愿意。”
“那怎么办呢?”
“她命运也够苦的!”
“苦瓜未必都能长在一棵蔓上啊!老弟!”
“我了解你的固执。”
“这种固执很廉价吗?”
“它很可贵。”我说,“但是你应当看到,因为过去的畸形政治而逃遁国外的人,有的今天回国参加建设……”
“我尊敬这些同志的回归,象尊敬陶莹莹一样。”他打断我的话说,“可是尊敬毕竟不是感情,我是和你谈我和她的爱情问题。”
我隐入了苦思之中。
“我几次去农场看她,她对我说他想离开这儿回砖厂去。我告诉她,你最近要来海滨小镇,她说她很想见你—面;现在她正在学校宿舍等候我们。”
列车喘着气,终于在滨临黄河的小站上停下来。
范汉儒替我提着旅行包,我俩匆匆走下被初雪覆盖着的站台。当我们来到他这间宿舍时,他的办公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大概是怕凉了,饭菜上都扣着盘子和饭碗——但她却不见了。
范汉儒去厨房——没有。
范汉儒呼喊她的名字——没有回应。
我突然从桌上的小闹钟下发现了一张信笺:
汉儒、叶涛:
原谅我不辞而别吧!
我很怕见你们——虽然我很渴望和你们在一起;但我走错了一步,无颜以对 “江东父老”了。
我对不起祖国!
我愧对生养的父母!
父母和我断绝了关系,是他们洁身自好,我很崇敬他们的行动。昨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县政委转给我的一张原机关重新审查我问题的结论:划我右派是错误的,但我的出逃同样是错误的。考虑到我的出逃“事出有因”,决定恢复我的公职—— 成为农场正式的医生。对着这张打字纸,我哭了;我不是委屈,而是感到无地自容。祖国宽恕了我,但我不能宽恕我自己。老范那两句话说得多么好啊!“别的错误都可以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不能自我宽恕的罪过。今天早晨,我来小镇以前,拿着我的结论去找了姜政委;你们能猜测到,我是请求他把我调走的。去哪儿?哪儿都行,只要离开河滨农场。姜政委最初很犹豫,但他理解了我的痛苦之后,当即和砖厂通了电话,决定下午用吉普车把我送回砖厂。
汉儒、叶涛同志,我从砖厂到河滨农场来,就是个错误。现在,理智告诉我,与其和老范离得这么近,不如远在天涯的好。令天,我怀着矛盾的心情来小镇和老范诀别,当然想见叶涛一面,但是见了叶涛我该说些什么呢!讲我为什么怕水—— 我是在出逃时的国界界河中被捕的;讲我为什么从不去黄河边上散步——我是黄河的不肖子孙!我很珍视汉儒同志给予我的感情,但我没有资格来获得!希望你们从头脑里抹去陶莹莹的影子吧!
我走了。
你们不要再返回农场来送我。来小镇前,我已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回农场后即刻奔赴晋北砖厂。原谅我,使老范为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但我要说,我不是存心欺骗一颗赤诚的心,而是因为我的错误实在难于启齿……
祝你们重逢愉快!
祝老范能获得幸福!
陶莹莹行前匆匆
宿舍内静极了,静极了……
只有桌上的小闹钟,在嘀嗒嘀嗒地鸣响着。
我们没有心情吃陶莹莹给我们准备下的午饭,一口气跑上黄河大堤。是想寻觅陶莹莹的踪影呢,还是想抒发一下感慨万千的情怀呢?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我们站在我们伟大的母亲——滚滚东流的黄河之畔,极目眺望着被初雪覆盆了的原野。
雪越下越大了……天是白的。地是白的。
片片品莹的雪花溶入了黄河,汇成黄河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造成了黄河的精灵。
我们两个“雪人”久久地站在雪地上,静听着黄河的涛声。它象述说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儿女的故事一样,奔腾咆哮地从我们脚下流淌而过,一直奔向东南……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