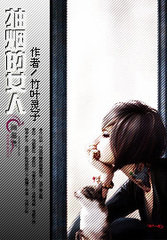纸上的美女_苏童-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劳 动的声音,也听见了一类诗歌高亢的节奏。
我是在阐述森林与诗歌的关系吗?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我生活在距离森林千里之遥 的东部城市,只能从家中的水曲柳家具上闻一下已经模糊不清的森林的气息。但是我还 是固执地说,我热爱森林,并且热爱着在诗歌中伐木的那些伐木工人。假如这样的说法 有点矫情,那不是我的错,是聂鲁达的错,或者说是诗歌的错。
现在不得不说到生态平衡、保护森林这种拾人牙慧的字眼了。稍有良知的人对此不 可能有丝毫的怀疑。长江、嫩江近年的洪水与周边森林滥砍滥伐有关,这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大兴安岭森林停止砍伐,这是关于森林保护的最新信息。我要说的是当我看见电 视里一个新闻记者手握话筒采访一个伐木工人,让他谈谈扔下油锯以后的打算时,我清 晰地看见那个伐木工迷茫的表情,然后他说,不伐树了,以后就种树了。
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想象中的某种劳动的声音嘎然而止了,某种诗歌的声音突然 暗哑了,聂鲁达在遥远的智利真的死去了。我觉得世界是现实的,讲究理性和科学的, 许多对劳动的赞美其实一厢情愿。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有一些劳动天生是错误的,就像 许多诗歌无论如何优美动听,它不是真理。我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森林之歌,以后关于森林的想象将不再是伐木和喊树的声音,在一个全世界植树的年 代,聂鲁达不得不去世,我们假如还要歌唱森林,必须要呼唤一个歌唱植树的诗人。
这是新的森林的诗篇。伐木者醒来!伐木者醒来了,醒来后他们就带着捆锯下山了。 这是由热烈奔放变得冷峻合理的森林的诗篇:伐木者醒来!大家扔下斧子油锯,回家去 吧。至于我们这些通过聂鲁达爱上森林的人,你是否要背诵这些新的诗篇,自己看着办 吧。
南腔北调
我最初接触到大批量的北方人是在北京求学时期,不管是何省的北方人,他们有一 个优势是我等南方佬望尘莫及的,那就是说话的优势,即使是来自东北腹地的同学,只 要轻轻把舌头一卷,再把行腔轻轻一扳,说出来的就是大差不差的普通话,而我们几个 来自南方的同学,即使你努力地把舌头搞得痉挛了,也不一定能说出普通话来,这个问 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感到深深的苦恼。
有一次寒假后返校,我把从家里带来的桔子拿出来给大家品尝,一个同学脸上露出 一种狡黠的笑容说,“你请我吃橛子?”我说,“怎么啦,你不喜欢吃橛子?”那个同 学突然生气地大叫起来,“你才爱吃橛子呢,什么橛子不橛子的?是桔子,不叫橛子!” 那位东北同学的叫声震聋发聩,使我一下面红耳赤起来,虽然我不是故意把桔子叫成橛 子的我也并不知道在那位同学的老家橛子的意思与排泄物紧密相连,但是我对自己的语 音从此有了痛楚的感觉。
后来我就一直努力摹仿几个北京同学说话,开始时舌头部位有点难过,惭惭地就习 惯了,不卷舌头反而不会说话。记得有一位上海同学,我们在一起时他说上海话,我说 苏州话,都是南蛮噘舌,倒也相安无事,但每逢有北京同学加入谈话,我们在说完一通 普通话后便忍不住相互批评起来,他嫌我乱卷舌头,我嫌他说话嘶啦嘶啦的,互相都觉 得对方说话别扭,又都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说得比对方好,结果就让那位京同学作裁判, 我记得他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说得还行,不过听上去一 个舌头长了点,一个舌头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大概是属于舌头短了一截的种类,就这样短着舌头说了四年的普通话,后来到了 南京工作,我已经想不起来刚到南京时是怎样说话的,据我的相交十余年的几个朋友回 忆,我当初是说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的,光听我说话没人猜得出我是南方人。朋友们 这么说,大概不是恭维。假如不是恭维,其中多少又揭露了我的现状,那些话的潜台词 是:你以为你现在说的是普通话,其实那普通话已经很不标准了。
大概是人乡随俗,我到南京没几年就学会了南京话,当南京话说得可以乱真时,我 的一口普通话就坐着火车返回北京了。有一次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打电话到我家,听见 我的声音竟然大吃一掠,说,“你的舌头怎么了?”我也惊谔,反问道,“我的舌头怎 么啦?”他说,“怎么又往前跑啦?又像南蛮噘舌之人!”这个电话让我百感交集,我 想这对于我大概是个无法置换的悲哀,我的舌头在经历了多年风雨后,又回到了它原来 的位置,说话时忍不住地往前跑,懒得再卷着吸着,它按惯性在我嘴里运动,我知道我 现在说着一口无规无矩的南京腔加苏州腔的普通话。
或许这不是我一人的悲哀,人们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适时适地变换语言,人永远都 比鹦鹉高明聪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南腔北调的缘故。
纸上的美女祖籍
人口流动有其悠久广阔的历史,假如追溯几代而上,今天的城市人无一例外地有着 一个异乡他壤的祖先,他的个人资料中出生地是a城,祖籍一栏中却是b城,对此人们已 经习以为常了。
祖籍对一个城市人意味什么?意味着某一个遥远的从未涉足的地方,意味着某一个 古代男婴在那地方狐狐坠地,意昧着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来处。
那是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它把城市入与陌生人模糊的家族,乡村以及人类迁徒史联 结在一起或者说它只是城市人身上形形色色标签中的一张,恰恰这张标签对他们的现实 生活是无足轻重的。
从前人们在旅途上闲聊,相邻而坐的人常常会向对方问如下的问题,先生哪里人? 答话那人报出的地名通常就是他的祖籍,从前在城市街道上很容易看见xx同乡会,xx会 馆这样的处所,从前的人们把老家,同乡的概念看得很重,这概念也在人们生活中成为 一种极为主要的人际关系,因此有许多集体行为的解释听来极为简单,我们是同乡,我 们是一个村子的。
如今在一些社交场合你也能听见类似的声音,哦,我们原来是同乡啊!但这种声音 的实质已经退化为一种虚无,就像美国人说nicemeetyou,如此而已,通常那两个人对他 们共通的故乡已了无记忆,他们可能根本没去过那里,故乡留给他们的印象只是一个地 名几个汉字,如此丽已。一切都依赖于在新的时代中的心态的演变,你可以想象在九十 年代,城市人是多么自觉的淘汰着情感世界中的多余部分!人们就这样奔走在祖先未曾 梦见的土地上,今天我们看见大批具有北方血统的青年男女匆匆行走在上海、香港、台 北的街道上,大批黑发黄皮的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南洋、欧洲、美国,你会在纽约第 五大道上突然听到熟悉的乡音,一抬头就看见了你的同乡,有时你们相视一笑,有时你 们形同陌路,一切都很自然,许多人已经抛弃了故乡,有时那是一种历史,有时那是一 种选择。
祖籍在哪里?在身份证上,故乡在哪里?在铁路和公路的另一端,同乡在哪里?在 陌生的人群中,只有他自己在自己的路上。
有些人走到天边也要遥望他的故乡,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旧金山一个留学生家作客, 她的房子紧靠太平洋的海湾,窗口海景美不胜收,房租当然很贵。我问她,既然经济桔 据,为甚么要租这么贵的房子,她说,这里能看太平洋,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知道, 海那边就是中国,我很想妈妈,我很想家。我一时无语,忍不住问,为什么不回去?就 一张机票的事啊。我看见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然后她轻轻他说,回不去了。 也许我的表情依然疑惑,她又补充了一句,其实,也不愿回去。
牛奶浴后上金床?
弹指一挥间,我们正处于一个贫穷与奢华并行不悸的时代,因此当报纸上披露新兴 的牛奶浴诞生时,尽管许多人瞠目结舌,许多人议论纷纷,但我相信还有许多人与我一 样,对这种牛奶浴内心是不以为怪的,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据说广东某地已经有入在推 销纯金制成的床,比起那种金床来,牛奶浴的奢华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我几乎可以肯定,闻听有人以牛奶洗澡而脸色大变的人,也与我一样,多为小时 候喝不上牛奶的人。
我们小时候喝不上牛奶,假如谁告诉我们某地某人在洗中奶浴,我们会断定他在谈 论平民们所陌生的宫廷帝王贵妇的生活。我们小时候只用光荣牌肥皂洗澡。假如谁来告 诉我们某地某人正在用牛奶洗澡,我们会失声大笑。
我们想能用上一块上海产的檀香皂已经美死了,用牛奶洗澡不是疯话便是梦话。
因此当我们得知牛奶浴即将应市时,我们愣然而愤怒,我们首先想到牛奶是一种高 尚的食物,是我们许多人童年想喝而喝不到的富有营养的食物,也是现在贫困乡村的孩 子们听说过却没见过的食物。想到浴室经营者们将把雪白香酽的牛奶一桶一桶地倒人浴 池中,想到许多散发着汗味和体臭(甚至长有梅毒和尖锐湿疣)的身体将浸泡在牛奶里, 想到那些被人体污染的牛奶最后将从下水道里汩汩流走,我们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我们不得不承认,以皂荚和劳动肥皂沈浴的时代已经过去,慈禧太后的香草浴盆也显得 寒伧而缺乏想象力,我们如此溯里糊涂地迎来了一个牛奶浴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我 们正处于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我们这些反对派倒显得有些心胸狭窄而又大惊小怪。
我们心胸狭窄是因为我们自己掏不出一厚叠钱去洗牛奶浴,还因为我们在家打开煤 气热水器,用力士香皂洗身,用飘柔香波洗头时,错以为自己进入了“小康”,而这种 错觉被牛奶浴彻底地纠正了一下,从此我们这些“小康”式洗澡的人将不敢洋洋自得。
我们大惊小怪是因为我们古典的良知或者顽固的大锅饭观念,我们会说,那么多的 中奶为什么要倾倒在浴池里?为什么不运到那些贫困的地区让那些半饥不饱的老人孩子 喝个够呢?但是牛奶浴的经营者们会说,那是希望工程和扶贫救灾的事,跟牛奶浴毫无 关系,你们所说的是无穷无尽的道义和援助,而他们所做的是无穷无尽的投资和获利。
况且牛奶浴的经营者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他们用于牛奶浴的牛奶是一种只对人 体皮肤有益的牛奶,假如喝到肚子里却营养价值不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种牛奶, 也不知道这种说这是否如今常见的商业口径和宣传策略,但我情愿相信那是真的,想到 那是真的,想到那牛奶并不怎么好喝也没什么营养,我的心里就舒服一些了。
我舒服不舒服其实无关宏旨,牛奶浴已经上市了,说不定也会像桑拿浴、冲浪浴什 么的一样风靡一时。我是不会去洗的,但总有喜欢新鲜事物的人欢呼雀跃着跳人那池牛 奶,总有雪白香酽的牛奶溅到地上,却溅不到你的身上,更溅不到你的嘴里。
我又想到广东的那几张金床,不知买了金床的人是否瞧得上牛奶浴,但我认为洗完 牛奶浴再上金床睡觉可以称得上丝丝入扣了。
虽然我们跺一跺脚便能洗上一回牛奶浴,却永远睡不上纯金制作的金床。
纸上的美女薄醉
我对于酒的态度向来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并非是由于我生长在江南地域的缘 故,江南也多好酒之士,我的两个舅舅都爱喝酒,通常是在餐前啜饮一盅两盅而已从来 未见他们有酩酊之状,我想要说南人北客饮酒的作风,我的两个舅舅大概是属于南方派 的。
我第一次醉酒是在大学期间,当时同学们都下河北山区植树劳动,有一天几个同学 结伴去县城一家小饭店打牙祭,一同学说要喝酒,结果就叫了瓶白酒,酒是当地的小酒 厂出的,名字却叫了个白兰地。第一次品酒,竟然品出个醇厚的酒味,再加上我们的古 典文学老师在讲解李清照词中的薄醉时声情并茂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 便有点贪杯,直奔“薄醉”的目标而去了。令人惊喜的是步出小酒馆时我果真是薄醉、 脚步像是踩在棉花上,另外几个同学便来扶我,嘴里快乐地喊道:薄醉了,薄醉了!后 来才知道那样的薄醉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学生时代透明单纯的心境一去不返,完全是 高梁酒的冒名“白兰地”也难以混入都市酒架之上,我在一次次的酒席饭局上一次次地 饮酒,渐渐地竟然对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