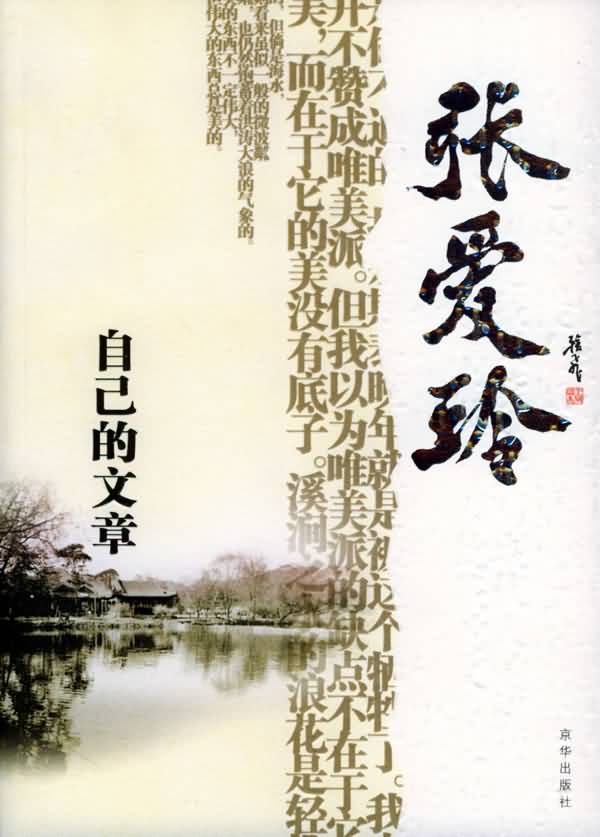笛安散文、诗歌和短篇集_笛安-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倒也还好。”我看着她,“不幸中的万幸,我已经没有父母了,他们看不见我现在的样子。”
在二十强进十强的晋级赛那天晚上,我知道我变成了孤儿。神明突然决定了给我的命运来一场龙卷风,拿走所有的一切。在后台的化妆间里,我接到了电话。我爸爸的公司在短短几天里就要破产结算,其他的股东们纷纷跳出来挖最后的一点墙角。我爸爸心脏病发,走的倒是没有痛苦。我妈妈神思恍惚地从医院走出来,他可能只是想走到对街去给我打个电话,但是一辆出租车撞倒了违反交通规则的她。依然可以用几句话,就说完了。
我挂断电话的时候,整个人都被掏空。我觉得我应该哭、应该喊、应该号啕、应该晕倒,应该茫然若失地掐自己一下看看这是不是梦。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我呆呆的凝视着巨大的镜子里的自己,穿着上台的服装,鲜丽的口红,眼睛周围画着浓重的阴影。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因为我突然觉得一阵奇妙的轻盈对我席卷而来,我沉重的肉体和灵魂都离我而去了,都随着我父母一起烟消云散了。我变成了镜子里面那个蝴蝶一般艳丽的歌姬。其实那个名叫廖芸芸的,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的女孩不过是这个歌姬的幻象,这个镜子里的蝴蝶是我廖芸芸苦苦做了很多年的南柯一梦。
既然什么都失去了,既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还在乎什么呢,还怕什么呢。归根结底,人生原本是幻象,归根结底,人们追的也不过是幻象。唱歌,唱歌吧。所有的幻想都能在那一瞬间变成握得住的,那个瞬间的名字,就叫颠倒众生。
然后导播过来了,要我准备上台。
这世上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人间已经换了,像换外套一样,轻盈地天翻地覆。一种强大的,坚硬的东西主宰了廖芸芸,那是种幻灭感,或者说,是幻灭尽头的自由,熊熊燃烧,坚不可摧,甚至抵挡了失去骨肉至亲的疼痛。
于是我走到台上去,我开始唱。以前我只知道唱歌是唱歌,可是知道那一天我才知道,我不是在唱,我是在让自己分崩离析。我的身体,我的整个生命都变得柔若无骨,任由我的声音随意的揉搓,就像一团泥巴,不在乎自己被塑成什么形状,也没有发言权。那个令人屏息静气的天籁,到底是我的声音呢,还是我的命运呢,为何我的意志这么听话,这么温暖,这么逆来顺受的接受它的摆布?你们欢呼吧,你们鼓掌吧,你们除了欢呼和鼓掌还能做什么呢,我就是你们在那个可怜的,全是幻觉的生命里能看到的最美的幻觉,负负得正,我就是唯一的真实。
可能是在那天,我才知道那道绿光是什么。是盼望。是让自己再也不是自己的,飞翔起来的盼望。我终于铁了心追逐得不到的东西了,我终于受到惩罚了。我终于一无所有了。我终于自由了。
当我发现我自己的脸上有两行泪的时候,音乐结束了。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欢呼,掌声,主持人的吹捧,评委们的惊喜。以及结束之后唱片公司的老板执意要马上去咖啡馆夜宵,为了讨论合约的细节。
我迟钝的说我想早点离开。我必须回家一趟,我没有说我的回家料理两个人的丧事以及一个烂摊子。导播惊讶地拍拍我的肩膀:“有什么事情能让你现在必须回家?这张合同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了。”
不,不是。除了唱歌,没有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合同,专辑,名利,全是狗屎。只不过为了能一直唱下去,我必须得到这些东西。
就在那天晚上,我看见了众生。
我们一群人坐在咖啡厅的包厢里,唱片公司的人,和被他们看好的新晋歌手。他们簇拥着我,告诉我我拥有光明的未来。比光明还光明,简直耀眼。虽然我只是十强,虽然不知道往后的比赛我能走多远,但是他们就是看中我了……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在楼梯拐角的钢琴边,看见了他。
他像是从天而降,像是遗世独立。他对我粲然一笑。他的英俊不是那种偶像小生的感觉。他的帅气非常真实,让你相信这样的英气来源于饮食男女的生活。他很会穿衣服。最重要的是,他熟稔地,不卑不亢的对我说:“你就是廖芸芸,我认得你。”
我认得你。他这样说,仿佛他早已认得我很多年。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后来的事也随着一件件发生了。
苏艳用力的捏了捏我的手腕:“好了,好了。可怜的孩子。什么都别再想。我全懂了。他是你命里的劫数。你呀——”这句“你呀”真是荡气回肠。苏艳伸出手,摸摸我额角的头发,“你呀,你知道不知道我见过好多赌棍?其实有的人虽然爱赌,可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不该。有的人不行,就像是被鬼附了身,不惨到底就绝对不收手,到最后活得像头牲口。你就是那后一种人。这跟人品好坏没关系,也跟懂不懂道理没关系,有的人生下来心里就有个能把持自己的阀门,有的人生下来就没有。芸芸,你好苦。”
“苏艳。”我对她笑,“大恩不言谢。”
“算了吧。”她也笑了,“我帮你,纯粹是因为当初我喜欢听你唱。你颠倒不了众生,你连一个叫众生的男人都搞不定。可是至少碰上了我,碰到了一个因为听过你唱歌就愿意帮你逃跑的人。”
“足够了。”我淡淡的说。
“不是真心话吧。”苏艳一针见血,“你这样的人,什么时候也不懂得知足的。”
“谁说的。”我不同意,“苏艳你能明白吗?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我为什么要唱歌。因为,”我笨拙的解释着,“比如说,小时候人们听说了我学校的名字才会夸奖我,长大了人们听见你上班的公司的名字才会认为你是不是精英,你这个人是因为那些标签才有意义。或者说,那些标签永远在那里,谁被贴上了谁就了不起。我不要这个,我厌倦了那套。唱歌就不一样,别人因为一些歌永远记住我,记住廖芸芸,廖芸芸这个人就是干干净净的三个字,不是什么学校的学生,不是什么机构的职员,提起那些歌,就是属于廖芸芸的。人生很短的,我不要再去迁就别人的标签,我的自己变成那个制造标签的人,苏艳,我说清楚了没有啊。”
我手指微颤,按灭了烟蒂。
“芸芸,你要的太多了。”她摇头,“做人不可以这么贪的。”
然后我们都听见了敲门声,我的另一个救星终于到了。
“叫他大伟就行。”苏艳看着那个高大、黝黑的男人。
他看了我一眼,毫不掩饰他的惊喜。
“我听苏艳说了,你是明星。”他说,像是要掩饰自己的窘迫,拿起桌上一瓶啤酒,用牙咬开了盖子。
“你敢喝。”苏艳呵斥她,“你在路上摔死了不要紧,你要是让芸芸有了闪失我要你的狗命。”
他讪讪地,用粗大的手指摸摸浑圆的额头,对沉默的小男孩说:“儿子,去给爸爸拿瓶汽水来。”
小男孩纹丝不动,眼皮都不抬一下。
“谁是你儿子。”苏艳继续啐他。
他呵呵的笑着,不以为意。
“该上路了。”苏艳握了握我冰冷的手,“一路当心。到了内蒙古你就得自己想办法了,放心,我会帮你留意他的消息的,万一他回来过,我会找人想办法带话,告诉他你在哪里。”
“我真舍不得你。”我说的是真心话。“
“不会再见面了。”苏艳爽利的说,“要不你这么匆忙,真想跟你要张cd呢。”
“我什么都没带出来。”我抱歉地说,然后,突然间灵机一动,“不过我可以给你唱。”
“真的呀。”她的眼睛也亮了,“那真的是太好了,我怎么没想到呢。”
于是,我就唱了。我在这个荒凉的城市荒凉的夜晚里,面对着陌生房屋里的杯盘狼藉,面对着三个萍水相逢的人,唱歌。
我唱的是我那张卖得不好的专辑里的歌,不是主打歌,却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叫《过路人》。
想起你,海浪的声音就在回荡。
吻我吧,别在乎那个过路人的眼光。
过路人,你为什么不走远。
难道说,看见一对恋人让你黯然神伤。
过路人,你知道我和他就要永别吗。
过路人,你是不是已经看出我眼里的沧桑。
过路人,你是否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过路人,别告诉我你知道的真相。
我只想让他抱紧我,带着我飞翔。
我只想从天上掉下来,掉进深深的海洋。
过路人,你是否了解眷恋的另一个名字叫绝望。
哀伤的过路人,你是不是我死去亲人的灵魂。
贫穷的过路人,你潦倒的衣襟上有颗纽扣在摇晃,
就像地平线上,苍白的太阳。
我唱完了。满室寂静。然后我听见了零零落落的掌声。小男孩笑着,把屋角一朵塑料花拿来给我。苏艳含着眼泪,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我们异口同声的在彼此的耳边说:“谢谢。”
于是我又要起程了。在夜色中,运货的大卡车发动的声音让人觉得很安全。
想起我们会在夜色中奔驰在公路上,就又让我觉得激动了,我又一次开始期待警察开着车在后面追我们,我们逃窜的时候和大卡车一起在山涧里面飞翔。如果我对人生还可以有什么期盼的话,我期盼,我能够死在黑暗的睡梦中。
我身边的驾驶座上,那个大伟有些羞涩地开口:“不瞒你说,刚才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还想着,这一路上,说不定我能找个机会,把你给弄了。”
“弄了?”我不解。
“就是占你的便宜。”他笑了,我一直看着窗外,不想去看他脸上的表情,“但是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一定把你安全地送到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唱得那么好听,你看见了吗,我的女人,我的儿子,都那么喜欢你。”
眼泪在这个时候倾斜而下。“谢谢。”我小声地说。我没有想到,其实我最初的梦想,最后还是完成了。
。 txtMt;Xt;小;说天;〃;堂
塞纳河不结冰
那家跟我们合作,负责我们旅行团晚餐的中国馆子,名叫“天外天”。是间川菜馆子,其中也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属于云南风味。离大名鼎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仅有几步之遥。两三天的旅程通常是这么安排的:圣母院,先贤祠,卢浮宫,塞纳河游船;然后是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再然后,蒙玛特,还有圣心教堂。至于观光红磨坊与否要视情况而定。最后的一天,当然是把全团的人都拉到九区来购物,看到“老佛爷”的招牌的时候,车里面一片欢呼声此起彼伏,就像是看见了一个失散很久的朋友。
当他们满载而归,心满意足地坐在“天外天”里面的时候,我通常情况下会长长地舒一口气。因为我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他们会上路继续往北或者往南,在每一个他们到达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导游在等着他们。
老板和我点一下头,非常有默契地,吩咐伙计们照着规定的团餐上菜。店里面因着我们的到来而喧闹起来的人气或多或少让小伙计们兴奋了起来。狭窄的餐桌下面,座椅旁边,以及一切能够用来放东西的地方都堆上了“gucci”,“cd”,“prada”,“chanel”,“lv”……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角落里面有几个年轻的男女,看上去像是两对,年纪大概都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们也是来这里吃饭的,似乎对我们这群人突如其来的喧闹有一点不满,以一种冷冷的审视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其中一个女孩子胸无城府地大声说:“喂,这些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国内的那些腐败分子?”她的三个同伴一边大笑一边制止她:“小声一点大小姐,这群人可不是洋人,听得懂你说什么。”
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留学生。我也看得出来,他们暂时还是快乐的。我对那个出言不逊的女孩子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张罗着整个团的人坐定:这边的两张桌子最好拼一下,那边的几个“gucci”的袋子是谁的赶快拿走,团里唯一的一个小孩子弄翻了茶杯,老板洗手间在哪里……当这一切都解决了以后,我不动声色地选择了一张离那几个年轻的孩子最近的桌子坐下。我喜欢他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这是我的习惯,我是说,每一次,当我带着一个团的人走进一家中餐馆,我都会习惯性地寻找有没有留学生。若是有的话,就想办法坐得离他们近一点。
因为他们的谈话总是令我想起我自己曾经的生活。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在巴黎做留学生。利用周末的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出来打牙祭。一边喝啤酒一边吹牛。那似乎是当时沉闷的生活里最大的快乐。现在,那种曾经让我厌烦厌恶以及厌倦的留学生的生活竟也变成了我非常愿意回忆甚至是怀念的东西。我想,这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