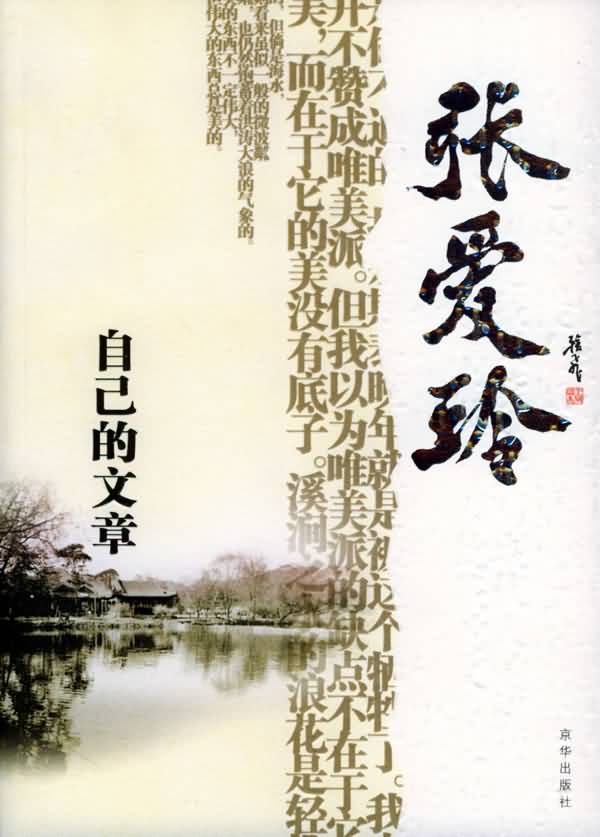笛安散文、诗歌和短篇集_笛安-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开他们的玩笑——虽然有瑕疵,可毕竟是礼物。放学的路上,我看着她从某个男孩的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以一种令人难堪的柔软的姿态和他挥手道别。“不害臊。”我在不远处“哧哧”地笑。“你懂什么?你个小屁孩儿。”李瞳高傲的仰着头。这样的对白当然不能被外婆听到——对此我们心照不宣。我已不记得有多少个午后,外婆在北方一泻千里的阳光下面一本正经地午睡着。李瞳牵着我的手,我们轻轻地穿过阴暗地门厅,像两个熟练地贼。关门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门锁地声音降至最低。偶尔李瞳会从外婆地小铁盒子里看似漫不经心地拿两张破烂不堪地零钱。外公地遗像在泛黄地墙壁上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对面墙上,还有一张黑白的周总理的照片。我很小的时候,总是搞不清墙上这两个黑白的老人到底那个是外公,哪个是周总理。李瞳就骂我“笨蛋,长的丑的那个就是外公。”
她是要带我去找穆成。在午饭后、下午上课之前那短暂的一个班小时,是我姐姐约会的时间。我不知道李瞳为何会选中了这个看上去平凡得令人失望的穆成,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她只好嘴硬地模仿电视剧里的台词:“在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中间,当然还是选那个爱我的,这样比较聪明。”这个解释令我肃然起敬,她居然有胆量使用“爱”这么不要脸的字眼儿。——我想我骨子里沉睡着一个乌合之众的灵魂吧,因为我本能地对所有出格的东西心存敬畏,哪怕是出格的不要脸。
穆成总是在红旗剧场的台阶上等我们。他等得无聊,就在那些台阶上练习轻功。我是说,像练习轻功那样轻盈的跳来跳去——一跃就掠过了好几级台阶。即使是今天,我也总能想起,在红旗剧场那颗硕大的五角星下面,有个男孩在百无聊赖的、专注的练习飞翔。姐姐张开双臂冲上去,却在离穆成还有两三级台阶的地方停下来,拘谨地粲然一笑。我是真的无比热爱这时候的李瞳——明明很不要脸,却又突然害起了羞。
“下午放学的时候过来看电影吧。”穆成邀请道,“明明一起来。”
李瞳故作矜持地撇嘴,“什么电影?不好看我们才不来。”
“好看的。《勇敢者的游戏》,美国片,说是惊险的呀。”穆成急切的解释着,“来嘛,我爷爷今晚不值班,值班的崔叔叔——”他一拍胸脯,“是老子的人。”
“你要做谁的老子哦?”李彤把头一偏,“不喜欢美国片,我爱看香港的。”
其实我和穆成都知道,她不过是拿一下腔调而已,她当然还是会来的。哪怕晚上回家的时候,又会挨外婆那种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咒骂。
穆成的爷爷在投降以后,鬼使神差的,又被派来打扫这座他曾经亲手插上白旗的楼房,看着这座灰色的三层建筑在一阵鞭炮声中变成了“红旗剧场”。卖票和领座儿的工作,他做了有半个世纪那么长。他是个可怕的爷爷,可怕的足以和我们的外婆相映成趣。我听到过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音量,在入口处的大厅里雷霆万钧地诅咒着那些逃票入场的坏孩子。他会很很多我听不懂的骂人话。我问过外婆那是什么意思,外婆说:“别说是我,就算只我的父母都未必懂得。”外婆还微笑着说:“阎锡山的老兵嘛,自然会将很有些年头的龙城话。”转眼间,她有板起了脸,“女儿家,打听粗话做什么?作死呢。”
【小柔给大家普及下地方知识:阎锡山是太原(龙城)解放前最后的军阀。】
夜晚,我独自躺在我和李瞳两个人的床上,倾听着外婆在屋外不动声色地挪动着椅子的声音。说是夜晚,其实九点刚过而已。外婆因为李瞳的晚归,脸色越来越难看。所以他要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乖乖的顺从了。这样就可以安然置身于风暴之外,甚至怀着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情期待即将上演的大戏。
“你又到哪里鬼混去了?”
“和同学看电影。是美国片,英文的。我们英语老师说,外语就是要多看外多的电影才学的好。”
“真的?”外婆的语气明显的在缓和,“在哪里看的?”
“在我们英语课代表家,不信,你打电话去问嘛。”李瞳他们班的英语课代表——还,真的是穆成。
“男的女的,哪个代表?”
“女的。”——你总算是撒了谎,我都等了这么久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她也没有讲真话。我们毕竟是天然的同盟,所以我下意识的忽略了这个谎言。她没有说她去了红旗剧场。外婆不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外公死在那里。1967年,某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外公像件落满灰尘的旧家具那样,被锁在红旗剧场三楼的库房,等待天亮以后的批斗大会。他趁着看守他们的人打盹的时候,从窗口跳了下去。其实那种高度,不是所有人都能摔死,我们的外公成功了。
这件事我外婆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李瞳的父母,我的姨妈和姨夫,他们恋爱是第一次约会,就是在红旗剧场看电影。外婆提起这件事,就拧着眉毛,咬牙切齿的对着空气哭道:“你自己亲爹的冤魂看着你们俩呢,你走进去的时候不嫌脊背上凉?”
爱情炽烈的温度一定是打败了老灵魂的注视。对姨妈和姨夫来说是如此,李瞳和穆成也一样。李瞳在黑暗中躺在我的肩边,发丝轻轻扰动着枕头。“《勇敢者的游戏》好不好看?”我羡慕的转过脸。
“他亲了我的嘴。”李瞳答非所问地说。
红旗剧场最后的夏天,就像一次深沉的睡眠那么短。好像是一夜之间,“红旗剧场”那四个大字就消失了,那栋沉默的灰色楼房变成一个大工厂,如同怪兽,整日咀嚼吞咽着电钻的声音,还有那些叮叮当当的敲击,以及,酷暑将尽的黄昏街头那个穷途末路的太阳。剧场里曾经的木制椅子被拆下来,一把又一把地,堆在门外的人行道上。白色的油漆刷出来的座位号似乎不那么适应明晃晃地室外光线。我和李瞳站在街的另一边,有些错愕地听着椅子之间的撞击声,那些清脆的声音的源头,基本都是连接椅和靠背之间那个活动的铁制合叶。每当电影散场,人们纷纷起立,那些椅子在一秒之内活了过来,迅速的、凶狠的、轻盈了起来,飞回到靠背上,像是遇到了节日。“南极城。”李瞳看着那簇新的,但是暗哑的三个大字,无不惊讶的说,“是一个新的电影院吗?”
几辆呼啸的“二八”自行车从我们眼前疾驰而过,集体捏闸的时候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凌厉的鸣叫。车上的那些男孩子们笑着,骂着粗话,只一瞬间,地面上就凭空多出了好几个还在冒烟的烟头。就像动物圈了地盘。他们是小流氓。不过我们龙城人不这么讲。龙城话管他们叫“赖皮小子”。这五六个赖皮小子从他们陨石一样的自行车上跳下来,带着因为飞驰而奔腾起来的温度,在我们面前灼热的戛然而止。
其中有一个,把眼睛转向了我们。那一瞬间我下意识的转过脸,捏紧李瞳的手,用一种看似若无其事的语气说“姐,咱们走吧。”后颈上却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火烫。可是李瞳却似没有反应,这时候,我听到了来自背后的声音。
“南极城不是电影院,小孩儿,是迪厅。”
“你说谁是小孩儿?”李瞳的声音里有种奇特的清澈。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怎么敢用这种挑衅的预期招惹他们?他们说不定会揍我们的。我见过一次,他们围着李瞳她们学校的男生,轻松的微笑着,从四个方向慢慢逼近他,毫不犹豫地踩着地上几滴新鲜的血。
“你连南极城是迪厅都不知道,还不是小孩儿么?”他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好吧,我也承认,这个赖皮小子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凶,并且,难以置信的顺眼,“小孩儿你是那个学校的?”
“你又是哪个学校的?”李瞳抬起眼睛,一览无余的打量着他。
“我?”他讽刺的笑了,“要不我说你是小孩儿。我不上学了,我是混社会的,你懂么?”语言间,掩饰不了的骄傲。他的那群朋友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距离,三三两两的站在红旗剧场——不,站在南极城的台阶那里,冲她大声嚷“你还走不走啦?x你妈。”
“x你妈!”他大声的、元气十足的喊回去,从刚刚的普通话,换成了龙城的腔调。然后他转过身子,以一个轻捷的姿态,冲他们奔跑过去。
“等一下!”李瞳甩开我的手,往上追了两步。于是他也停了下来,猝不及防的、明亮的转过脸庞。
“十四中,开学上初三,李瞳。”我的姐姐说完这句话,就拉着我头也不回的飞奔而去。龙城的夏日是凝固的,蠢蠢欲动的东西,只有我们鼓满了风的裙子。
“我叫潘勇——”那个声音追了上来,伴随着更远处赖皮小子肆无忌惮的哄笑声。
潘勇和李瞳的名字,一年后,在那个圈子里变得无人不知。“南极城”舞厅是他们所有人的疆域,城池,以及创造奇迹的地方。那年头,龙城人还不会说“夜店”这个词,“迪厅”在我们这里,已经是离激情和堕落最近的词汇。按理说,那不是未成年人还去的地方,可是,谁知道我们龙城的成年人们都在夜幕降临之后躲到了哪里,要是没有这些赖皮小子,以及坐在他们自行车后面的姑娘们,谁知道南极城还能不能如今日一样,活在很多人尽管蒙尘,却从未消亡的记忆里。十五元一张的门票挡不住他们。后来涨到了二十元也不行——他们有的是办法搞到钱,五彩的霓虹灯在古老的街道上嚣张却宁静的闪烁着,可是里面却换了人间。音响粗糙,不过胜在霸道,鬼火一般蓝色的荧光切碎了那些扭动着、舞蹈着的年轻的躯体,震耳欲聋的音乐就是从那些破碎的躯壳里流出的血,可也是这音乐,成了代替血液注入那些躯壳里的灵气。想要说句话就必须大吼大叫着,但是何必讲话呢?舞池的另一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瓶碧绿的啤酒像花那样,柔弱无骨的绽放了。甩出来新鲜的、璀璨的白色泡沫。都是柔弱无骨的。只有简短有力的超重低音是南极城的夜里唯一一样坚硬的东西,它是所有舞蹈的骨头,每个人都在跳跃摇摆的时候踩着它,就像踩着自己的心脏。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时候的南极城,我不敢,同时我可不能在夜晚的时候逃出去。家里总要有个人为夜游的李瞳望风,或者打掩护——不,算了吧,我就是胆怯。我还是迷恋着当外婆破口大骂的时候,胆战心惊地缩在小屋里,暗自庆幸着,还好我是个“乖孩子”,我可以躲进这三个字里遮风避雨。
所有关于南极城的故事,都是李瞳告诉我的。她带着一脸刻意为之的沉着,声音中却是掩饰不了的欢愉,以一种内行人的姿态,给我扫盲。“咱们龙城主要就是这三个帮派的人——”她的口吻简直称得上循循善诱,我再一次被征服了,因为她又使用了一个让我肃然起敬的词汇,“帮派”。“北城区那边最厉害的就是赵锋,大家都叫他赵疯子,他手底下主要就是四个学校的人。北城的人都讲普通话。南城区数的着的就只有潘勇的老大了,他叫宋凯。其实你也见过他一次的。不过,”李瞳得意扬扬地斜睨着我,“宋凯那个人虽然能打,也豁得出去,其实脑子很笨的,特别二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才都叫他‘二凯’啊——这么叫惯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姓宋。就是因为他笨,所以他很听潘勇的话。南城这边的人都是讲龙城话的。再剩下的就是西边铁路局那边的小孩了,是讲东北话的,他们的父母好像都是从那边迁来的吧——你不知道,他们讲话的时候真的都和赵本山的小品一模一样……”“可是,潘勇和你说话的时候不都是说普通话吗?我听见过他说龙城话的,其实——怪怪的,他说的不是特别好。”我托着腮,不耻下问。“这个——”李瞳露出一点儿为难的深情,“告诉你也不要紧。潘勇原本是混北城的,所以他原本的老大是赵疯子,可是,赵疯子当时的姑娘看上了我们潘勇——”“啊?”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要脸!”他们俩的道德观让我立刻认定了,赵锋的那个姑娘是个“骚货”,潘勇也自然而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我这么想的时候显然忘了,我的姐姐其实也做了和那个姑娘一样的事情。话又说回来,“道德”这东西,本来就是用在陌生人身上的。
“喂,不能那么说的。”李瞳轻轻打了一下我的肩膀,“关潘勇什么事啊?潘勇又不喜欢她,不过赵疯子不相信。那段时间赵疯子真的疯了,到处放话说要剁了潘勇。那些人成天四处地找潘勇,想要堵他。潘勇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二凯的,还帮二凯约到了一个在溜冰场认识的姑娘。从那以后,潘勇就来混南城了。”李瞳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