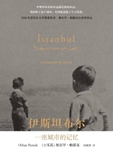j.斯坦利先生的证词-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黑暗里跳动,“顺带一提,我叫杰森。”
“斯坦利。”
“从来不喜欢这种派对,”杰森吸了一口烟,“都是一个样,太多酒精,太少真正的谈话,我每年都告诉自己不要再来了。”
“说得好像你参加过很多毕业派对似的。”
“三次。当你运营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实验室时,这种派对就是寻找便宜劳力的最佳场合,”杰森揪下襟花,打量着它,好像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手里,“假设你足够好运,还能从喝醉的院长那里捡到一些经费的碎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叫我‘乌鸦’,听过这个绰号吗?”
斯坦利摇摇头,掸掉烟灰,“那你的运气如何?”
“时好时坏。”
“人生。”
“人生。”杰森附和道,又深吸了一口烟,“新毕业生?”
“属于你在找的‘便宜劳力’吗?”
“取决于你能不能在实验室里帮上忙,”杰森把烟摁熄在砖墙上,看着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你能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生命科学院的毕业生,也许能做一些扫地之类的工作。”
杰森大笑起来,“我敢肯定你能的,”他从衣袋里摸出钢笔和一个小小的日程本,撕下一页,潦草地写下一个号码,“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的实验室——准确来说是我和辛克莱的实验室,但真正提供智力的是我——它叫IntelGenes,在韦洛克院长眼中肯定不比一套儿童化学玩具好多少,但我们在做真正令人激动的玩意。”
斯坦利接过了那张纸,“谢了。”
他推开门,前厅的灯光涌出来,照在台阶和修剪整齐的灌木上。杰森叫住了他,斯坦利转过身,一手扶着门,挑起眉毛。
对方并没有马上回答,借着灯光打量他,不管他想在斯坦利脸上找的是什么,他似乎是找到了。“这个问题也许听起来很怪,”杰森停顿了一下,“但你的名字不会碰巧叫加斯帕吧?”
——
他们最终找到一家安静的酒吧,很小,几乎只是墙上的一个钉孔。酒保专心致志地看着桌球锦标赛重播,几乎没有留意到他们。那台固定在吧台尽头的电视图像模糊,时不时就闪动一下,缓慢地变成怪异的蓝色,被酒保的拳头砸几下之后才慢吞吞地恢复正常。
杰森要了马丁尼,斯坦利点了一杯螺丝起子,两个人都并不真正关心自己喝的是什么,只要里面有酒精就行了。斯坦利能看出来他们为什么完全没认出对方,面前这个杰森·科尔曼身上已经不剩下多少当年那个热衷谈论木工和南美雨林的男孩的影子,全是严肃的棱角,但又被一种久经演练的、推销员式的微笑所中和。那种固执的引力还在,悄悄地拉扯着周围的人,试图改变他们的运行轨迹。斯坦利思忖着自己改变了多少,两年前,因为急着摆脱“无聊”的评价,斯坦利一度把头发染成蓝色,复活节假期回家的时候父亲震惊地看着他,并没有说什么。一个月之后他剪掉了那些染色的头发,自此再也没有对它们动过手脚。萨莎喜欢斯坦利的沉默,“喜欢”的意思是,她从来没抱怨过。不,斯坦利告诉自己,萨莎走了,他不需要再遵守她的标准了。
“你没有怎么变,只是,你知道的,长大了。”杰森把餐巾折起来,又展开,他的手从来都闲不下来,“九年了,嗯?我猜你的父母终于厌倦了圣马洛。”
侍应送来了他们的酒,又回到电视机前,心无旁骛地看斯蒂芬·亨徳利逐一把红球击入球袋。斯坦利用食指抹去玻璃杯上的水珠,“他们85年年底分居了,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后来的暑假我都在‘狗□□’里帮忙——抱歉,那是家爱尔兰酒吧的名字,老板是我爸的朋友,养了一只大丹犬。”
杰森用牙签拨弄杯底的橄榄,“我很遗憾。”
“父母的部分,还是狗的部分?”
“各有一半?”
“三七分比较适合。”斯坦利喝了一口酒,橙汁加得太多了,“你们后来还住在同一家旅店里?”
“对,直到前年我们都还在那里度假。尼娜偶尔会问起你。”
“尼娜?”
“双胞胎里的妹妹,我以为你会记得她,我们去灯塔的那天——”
“别,”斯坦利脱口而出,惊讶于这些遗忘已久的沉渣仍然能让他耳朵发热,“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经历。”
杰森冲酒杯笑起来,戳起酒渍橄榄,咀嚼着,“也许是我最好的经历之一。”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比另一些幸运。”
“从来不相信运气,”杰森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这里堵着些不可知论的水泥。”
“听起来对你的研究不是很有帮助。”
“帮助我们保持谦卑。”
“很公平。”
他们碰了碰杯,换了个话题。杰森开始谈论实验室、合伙人辛克莱和他们的病毒学研究,就像当年谈论那个改造成工作室的旧棚子,带着一模一样的热情。莱恩·辛克莱是杰森的大学室友和IntelGenes的主要投资人,诚实地说,他也是唯一的投资人。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一点点地买需要的设备。“技术上来说,我从来没有摆脱破产状态,一切都很贵,不管你怎么会说话,认识多少人。有一次我们炸毁了一个保温柜,我会让辛克莱给你讲这个故事,他说得更好笑,不那么像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我们都被隔离了两个星期。”杰森喝掉了最后一点马丁尼,“你会过来看看的,对吗,就明天?”
“为什么不?”
这是个错误的选择,一条丛林里的小路,隐约露出弯曲的轮廓,但在1994年夏天斯坦利仍然看不见被枝叶遮挡的断崖。他抬手叫来侍应,点了第二杯酒。
☆、4
4。
莱恩·辛克莱身高只有五尺六寸,长着容易讨好人的圆脸。当斯坦利在实验室门口被雨淋湿的台阶上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对辛克莱的第一印象是某种啮齿类动物,小而温和,对世界唯一的要求是一个核桃。地下室的铁门上着一把普通的挂锁,更像是个放拖把和旧轮胎的杂物房。辛克莱花了令人尴尬的十分钟寻找钥匙,最后还是不得不从旧花盆下面摸出了备用钥匙。杰森和他共用一个充当办公室的6x6小隔间,这里面就像个爆炸现场,那两张摇摇晃晃的书桌就是爆心,堆着稿纸、铅笔、铝制汽水罐、塑胶玩具、发霉的马克杯和折角的期刊,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还有一小罐虫蛹。靠墙放着一个巨大的保温箱,日光灯照亮了一段粗壮的栖木。
“玉米片。”辛克莱说。
斯坦利转过身,“抱歉,什么?”
“蜥蜴的名字。”对方指了指保温箱,斯坦利这才留意到懒洋洋地趴在木头上的小型冷血动物,“他一次能吃半袋玉米片。”
“他不能,别再乱喂他东西了。”杰森插嘴,玉米片冷漠地转了转眼珠,挪动了一下,让日光灯直射它那生长着许多小突起的头部,“这边,加斯帕。”
——
“我离开了小隔间,跟着他去消毒室。我原本以为他会带我去看样品——那时候‘红箭I’的研究已经接近完成了——但并没有,我们只是隔着玻璃看了一眼设备,像在动物园里看鲸鲨似的,‘请勿触摸玻璃,不可使用闪光灯’。杰森说他和辛克莱正在合写一篇‘关于疫苗的论文’,含糊其辞,不愿意泄露更多的细节。你看,吉布森小姐,杰森并不轻易信任别人,更准确地说,我不认为他真的信任过谁,不是我,不是辛克莱。他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像个电影明星,人们说这是魅力,我把这叫作表演天赋。”斯坦利咳嗽起来,在床头柜上摸索着,律师把装着水的杯子递给了他,“谢谢你。他们原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投稿,但事实上那篇论文整整三年之后才发表,我们的第一颗石子,打出了漂亮的水花。97年是一个好年份,吉布森小姐,杰森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IntelGenes注册了第一个专利,搬出了地下室,租了个稍微更靠近市区的地点,一座平房,借用辛克莱的话来说,一个‘水泥做的鞋盒子’。原本是个诊所,一个私人执业的牙医在这里补了三十多年龋齿,带着积蓄搬到卡迪兹去了,我听说。总而言之,IG第一次获得了关注,更重要的是,投资。”
“你的意思是吉姆·佛莱特从1997年开始就和你们有资金往来?”
“佛莱特?不,那是IG控股公司和基金会成立之后的事了,控股公司是佛莱特的主意,基金会是杰森的,不管怎样,为我们付账单的都是老吉姆。杰森多半是在哪个鸡尾酒会上认识他的,我在辛克莱的婚礼上才第一次见到他,这人似乎能凭空变出钱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钱的来源,那就是在撒谎了,但2000年左右IG在试图收购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小公司,我们需要那些钱。”斯坦利把空杯子放回原处,双手交叠在被单上,“我和辛克莱是基金会的主席,但我们都明白实际的权力落在哪里。辛克莱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最小的一个是女儿,上帝保佑他们。你可以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几乎不再参与IG的运营了。事实上IG膨胀得那么大,有时候我觉得是它在‘运营’我。”
“你在2007年辞职离开,”吉布森翻着文件夹里的资料,“这听起来不太妙。”
斯坦利张开嘴,却被短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护工没有等待回答就开门进来,一言不发地从推车上取下托盘,放到斯坦利面前。当天的午餐是马铃薯泥和盐水煮四季豆,斯坦利直接把食物推到一边。
“你应该吃一点的。”
“假如控罪成立,我会有足够的时间尝试监狱伙食,现在就不了,谢谢。”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具体哪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枪杀杰森·科尔曼。”
“我正准备说到那里,”斯坦利指了指杯子,吉布森重新给他倒满水,放到餐盘旁边,“这是从丹尼·马瑟尔和‘剃刀’开始的。”
——
领带打得太紧了,斯坦利抬手想拽一下领口,及时阻止了自己,假装在看手表。一个非正式的鸡尾酒会紧接在发布会之后举行,IG研发中心大厅一向空旷得像片盐碱地,此刻人满为患,斯坦利能认出一些记者和见过几面的制药公司代表,至于其他人,他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研发中心几个月前才投入使用,一个匍匐在山地上的三层建筑群。斯坦利的办公室在三楼,假如天气好的话,能越过起伏的树冠,看见远处湖水的微光。他希望现在就能躲回去,远离人群,把堆积如山的报告看完。在临时支起的大屏幕上,IntelGenes的宣传片第五千次开始循环播放,那些被过度抽象和美化的脱氧核糖核酸链在屏幕上懒洋洋地旋转。“备受瞩目的‘红箭’项目,”录音雀跃地说,带着一种保险经纪式的乐观,“以及全新的‘光子’项目,在IntelGenes,我们有责任为——”
斯坦利闭上眼睛,他的头开始疼起来,并不严重,也许只是想象,而非实质的痛楚。他拦住一个侍应,从托盘上拿了一杯新的香槟。
有人碰了碰他的手臂,杰森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押进人群里,“看我抓到了谁,”他向他的行星们宣布,用力拍了一下斯坦利的后背,斯坦利差点把香槟泼到自己的前襟上,“加斯帕,这是吉姆,你当然认识,你们在莱恩的婚礼上见过面。吉姆这几年帮了我们很多忙,不是吗,吉姆?”
吉姆·佛莱特头发灰白,看起来就像个公学教师,那种毫不犹豫地罚留堂的类型。他打量人的方式令斯坦利想起鱼鹰,举止也带着一种和鸟类相似的神经质。他和佛莱特握了握手,表示当然记得,感谢他的投资。对方的回答是举了举酒杯,移开了目光。
杰森继续把他介绍给其他人,白厅秘书梅琳达·塔克,GSK来的“艾迪”,市场部的戴维·舒尔茨,斯坦利机械地和他们握手,转头就忘了他们的脸和名字。杰森又开始讲多年前那个不慎炸毁保温柜的故事,所有人都在笑,多半是出于礼貌。斯坦利借口要续杯,从包围圈里逃出来,走向冷餐台。
“斯坦利?”
真是没完没了,斯坦利转过身,扫了一眼对方胸前挂着的访客通行证,“听着,如果你想进行采访,需要先联络我们的公共关系——”
“我是丹尼·马瑟尔,《新观察者》杂志,”圆形眼镜和滑稽的尖鼻子令记者看起来像个漫画人物,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斯坦利,在得不到预期中的反应之后才补充了一句,“‘猪崽’,你记得吗?”
猪崽,这个绰号在斯坦利脑海里总是和黑漆漆的宿舍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丹尼总是像畏光的真菌一样待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