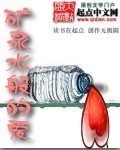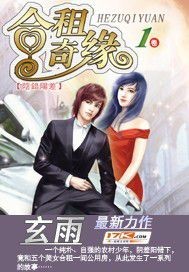����ʱ���İ���-��7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ȡ����ҵ����ֻ���һ����������������һ���������������������������ȥѰ���ʵǡ���������
�������Ժ�����ص���˼����Ȼ����������ֵĽ������һ�æ������������������ֻ����ͷ���Ĺ�ţͷ��˦��β������һֻɹ�˺ܾá����ӱ��Ϳ����ࡢ��ʣ��һ��ͷ�ǵIJк���Ȼ��ţ��ǰ����ڵ��ϣ����ص�˻�л���
�����������ľ���ֻ�����е�ţȫ���������������صؽл������ƺƵ�������ɽ�ӡ����룬��ν�ľ����������Ҳ���������������ij���ɣ�
���������Ҿ�����ǣ�ţ���۽Ƕ�����ˮ�����ʡ�һͷ����ͷ����ͷ������һ·���ӹ�ȥ�����е�ţ��Ȼ�������ᣬΪ������ȥ��ͬ�鱯�ˡ��Ҳ�֪������ͬ������ô���ģ��������ǵľٶ�˵�����������ڼ����Լ���ͬ�飡��һ�ٶ�����Լ������20�����ӡ�
�������ſ��ţ���֪Ϊ�Σ��ҵ��۽Ǿ�Ȼ��������������ˮ��
�������������У��ҿ�����ţͷ����վ��ҡ��β�����Ƕ��С���ʱ������ţ��վ�������ˡ����˺ܾúܾã���ԭ���ƺ����ڵػ�������ֻ��ţ�Ľл���������DZ�׳�������ģ������������Ⱥţ���ģ�Ҳ�ڿ�����������������ġ������룬��Щ��������̡�����µĶ�����ǿֲ����ײС������Ҷᣬ�������������Dz�ɱͬ�ࡢ���ֲ�������ɱ�������ǿ�֪�����ٹ������꣬���绹������������Ҫ���±��������ֻسɶ������ô�죿��Ϊ������ϧ��Ϊ���DZ�����������ʱ����ֵ��룺��������������ܵľ��������ж�ã���Ҫ����Щ������ɱ���������ȳ��������������뷼�������������ڵ����ޡ���
���������ұ���Ļ���Ķ��ǵij���������ס֮�ʣ��ҵ�����Ҳ����������ţ�к������ߣ�����������ζ��ͻȻ���������ţ��۾����ţ�����ë���ǿ�ð�Ŵ�������һ�����������Ͻ���������֪���������ˣ�����һͷ��������������Ȼ���������������������ˡ��ұ�Ͻ���������ţȺ���ˡ�
�������������ϣ���ȴ����ס�룺����֮��Ҳ���ھ��춯�صĸ��飬�����˺�����ϧ��������������������֮��ĸ����������Ť����������������ʱ��Ŀ��飬�������*������á����桢������ϵ����������ĸ����Ѿ���ë��ǣ����پ���
�������һ��ĸ��飬�Ҳ���˵���춯�أ����������ܹ�������ʱ�յĿ��飺ʱ���ϣ��ҿ��Ե���һ�ꡢ���ꡢʮ�꣬���µȵ�����Ҳл�ˣ���Ҳ�ִ˲�ƣ�����ȴ���Ҳ��һ�ְ����ռ��ϣ�����������ãã��ԭ�����Ǻƺ�ɳĮ�������ã����ǵ�����ֻҪ֪����ŵķ�λ����һ������ҹ�������ͣ��ظϵ��������ߣ�
�����Ҷ�����ţȺ�ϻ�ס��������ĺɫ����
�������°��ҽ�ţ�������ڣ�������������ϴ�����ڲ�ԭ�ϣ�����Ȼ����������ϴ����ϰ�ߣ���һ�����Һ͵��ص�������Ȼ���졣��˵��ԭ��һ�����У���ϴ�����裺������ϴһ�Σ����ϴһ�Ρ�����������ĸ�Ů���ںӱ�ϴ�裬�Ǿ�˵�����Ͼ�Ҫ�����ˡ�������˵����ޣ���˵�Ǹ�ϴ��Ĺ������ʱ���ķ�չ�����˵����Ȼ��ʧƫ�ģ����ڲ�ԭ֮�ϣ�ϴ��ȷʵ�ܲ����㣬�������ں�����ﶬ������֮�ʡ�
��q�Шr���q�Шr��ӭ���١�������������
���u�����������q�q��������������������
�������������t��������
�����������p�p�p�p�p�p�p�p�p�p�p�p�p�p�p�桡Ȩ���顡ԭ��������
��������������������������������������
�����������ֻ����ʡ�m����
�����ƻ�������011��
����ϴ���������Ѱ��ź����͡��ְ��⡢���Ƶ�ţ���䡢ţβ�ͣ�����Ũ����䣵����̾ơ����̾Ʒ������ɹ�����������ں������С�����ˮ�ݣ��������ҡ���˵������������ҡ�����ָ�̾ơ������������ɣ�����������̾Ƹ���úȣ���������̰�����ٿ�֮�ʣ��Ҳŷ��ֽ���������ƺ������ʢ�����µ���ɫҲ�ƺ����⾫����һ�ھƣ���Ц������������ʲô������
����ҡҷ�ĵƹ��£�����Ц������ֻ�Ǵ��ҺȾƳԲˣ���������ؽ��˼е��ҵ�����������ƽʱ���һ�̹Ȼ���ܣ���Ϊ���Dz�ԭ�˵����飻���ǽ����������ڼң��Һ��¹��й�Ů�ģ������������е���Ť�������Ҷ���û��˿������Ȥ�����������棬ȴ��һЩ��������ͷ�����������ݼ��ţ�������������һ���������������棬�����������ʵ�⻬��*�����Һܻ���������а������ʱ����Ŀ�������Ѳ���������������Ϻ��ֱײ����ȴ����û�а����Ǹɳ�����˼����������Ժ���Ŀ���ø��ӳ���ƽ�ͣ��������ƽ�����棬����һЩǧ��ٹ�Ī�������˼�룬�·���а���Ԩ��һ�����̣��Ʊغ�ˮ���죬���ij��֡���ˣ��ұ������������ɼ�̵ij��̣��������������ı�����
�������ڣ��ҷ��ֹ����ƺ��빥���ҵij��̡���������ͨ�죬�۲�����������Ǯ�����IJ��Σ�һ�˽�һ�˵س������������ֺ��������������������Ƶ�����ľ��������µ�ս����������ãã��ԭ����
����Ϊ�˱������ʪ������������֮�£��ҴҴҺ��걭��IJоƣ����������´DZ�
�����ص��Լ����ɹŰ�����Ҳû���Ƶƣ�ֱ�Ӻ������ڴ��ϡ�����ղŴDZ��ʱ���º���ʮ��ƽ������û��ʧ��֮ɫ��Ҳû������֮�⡣����������Լ�����һ�٣�ħ���������������������Լ��ں�˼������ˡ������ԴӺ�ǰŮ�����˷��֡��һ����Һ����Ժ���*���棬���൱�͵��������Ϲ��ſ���ɮ��Ľ���������һ���һ���ʱ���ҹ�Ȼֻ��ݺݵ��మһ�����Ƚ�������а���������һ��뿪���Ѿ��ܳ�һ��ʱ�䣬��������һ�������������������ˣ����ǵõ������˾��ӡ��ۼ������ģ����������ˣ��Ǻǣ���������ο�Լ���
������ȼһ֧�̡�ͨ�����ͷ����ظ��ںڰ��У��·����鶯ʱ��*����
������������Ƿǣ��������ٵĽŲ������漴����������һ����Ӱ���Ȱ����˽�����
�����������Ĺ��ߣ��ҷ������˵�������ϡ���ǹ��¡��һ���֮���Լ����������𣬸ɿ�һ������˭��
�����������ǹ��£����ƺ��е����⣺�ף��㻹û˯������Ϊ��ղŵ���ס���������Բ��ż�����˯���ء���
��������Ȼ�ľ��������Ҳ߯ɫ�����죬��Ȼ���ˮ���㣬���Ҳ�ʤ������ʱ�����͵������������������ǿ�����ҳ��ҡ������ֱ��*��ıƹ������ϻ��������������Dz�è���Ұ�����ͷŭ�𣬵������ߵ��͵ƣ������ض���˵������ô���ˣ���ʲô����β��ȵ����������˵��
������ƵĹ�Ȧ�У������Եü������ͣ�ֻ����������Ӳ�ĺ���˵�����������ˣ�
���������´������ԭ�ϵ�Ů�����Ƿ�����˼���ѵ����ǵ�������������ˮһ����ֻҪš����ͷ���ͻ��������ʲ�ͣ����ˮ��Դȷʵ�ḻ�ÿ��ԣ������ܵÿ����˼��Ƿ�����ȱˮ���аɣ�������֪����������ȱˮ�����͵ģ������ܵÿ����˼��Ƿ�ֻϲ���ȶ�����Ͱװˮ�ɣ�������Σ��������������һ����Ը�����籡�������ء�
���������ڲ���˼�飬˭֪�����ֽ���˵��һ�䣺������ȥţ���һͷĸţ�Ѳ�������Сʱ�ˣ�
������Ī�������˵���ҵ�רҵ�ֲ��Ǹ����ƣ�������ȥ����ʲô�ã�Ҫ��ȥ����ҽ�ɣ���
�������¹������ң�Ц��˵�����������ˣ������϶��ܰ���æ�������߰ɣ��ٵ�����ȥ��ĸţ��Сţ���������ģ�
������һ�����о����»�ͦ���أ������Ź�����ţ���ȥ��
��������ţ��ҿ���ţ�е�һ��������ĸţ*���棬�������ѣ���ͣ�س鴤��ĸţ�Ѿ�����һϢ������һ��̲��Ѫ����Ȼ�������������������ֳ��滹����ʮ�ֽ��ţ��ҶԹ��±�Թ���������������⣬��Ϊʲô����Щ���Ұ���
��������̯̯˫�֣����ؽ��͵�������Ӱ������Ϣ��ղ���һ����æµ���죬����û�ܰ������á���˭������Ů���أ�˭�����������أ�
�������������仰�ƺ��������������ұ�ĸţ�Ѳ��ij�����һʱ��û����ס��
������ߣ�����ӣ��ڹ��µ�ָ���£����ý�����ĸţ��ƨ�ɣ����Ű�ţ�е�С������ĸţ�ӹ���Ȼ�������ȥһת��ţ�е�ͷ����¶�˳������漴�������嶼����������
�������²�����ϧ��˵��������ͷС��ţ����
�����Ұ�ʪ���ܵ�Сţ�в��ɣ��������£����������ɹŰ����ñ��Ӹ���ȡů�����½ӹ�Сţ�У�ȴվ�Ų�����˵�����ǵð�����ɱ�ˡ�
�����ҳ���һ�����������Dz��̺�ɱ����ͷСţ�ո��������������Ҫ��������ţ���������ô�ó��������Ƿ��ˣ�
��������ҡҡͷ����ͷĸţ�ǵ�һ����Сţ�������Լ��Ķ��ӣ����Dz�ɱСţ�����Լ�������ҲҪɱ���ġ����У����Dz�ԭ����һ����ͳ��ţȺ������ĸţҪ���£��ŵ�ţȺ�����ڣ�Ҫ�����¹�ţ����ɱ����
�����Ҽ������ͬ�⡣��ͷСţ���������ֽ����ģ���ô������������ȥ����������Σ����ô���һ���������������������������Ȼ����ʮ�������ɹ������ů�����⣬Ҳ�Ǻõġ����⣬�������Ƕ����������������ģ����ֹ����
�������ҵļ���£�����ֻ�ð�Сţ�зŻ�ţ�����ŵ�����������ߡ����Ҿ�����ǣ��ղ�����������ĸţ��Ȼ�����Լ��������ӣ�����������ţ��ȥ����Сţ�У���ţ��ȥ������
������һĻ���ҿ���Ŀ�ɿڴ������������ҵĸ첲���㿴����û���Ѱɡ����ǸϽ���Сţ��ɱ�����ٹ�һ���������Ҫ��������ȵ�ϡ���ã�������û�����ˡ�
�������ŭ�ص��˹���һ�ۣ���������������ԳԳԣ����˳ԣ��㻹�ܲ�����������飿
��������һ㶣������漴����һ˿�ƻ��Ĺ�â����������ͷ˵���������Сţ���������ˣ����������ˣ�Ҳ���ᱣ���㡣
������ʱ����Ϊ���ǹ��µļ�����˭֪������֮�����Ҽ����뿪���ױ�����ԭ��ǰ���죬����ţ�У��Һ�����С��ţȡ���dzƣ����汣�����ҡ��Ǵ��ǵ���һ��ç���۸��ң��������������������������ܣ�����ˤ�ñ������ס�������ʱ�������ߵ�����ţ�У���������Ѿ��г���һͷ���ţ�ˣ�ŭ��������ͻȻ������ȥ��β��һ����°�ĭ��һ��ͷ������δ�����Ӳ��Сţ�Ƕ��˹�ȥ����һ���Ӷ������ţ�ֱ�Ӷ����Ǽһ��ƨ���ϣ����Ĵ糤��ţ�Ǵ�����������ʹ��������ʹ�С������ֵ��е�������˰�æ������ţ��ק�����ҿ����Ǽһ�һ��ƨ��һ������������Ѫ���졣��ʱ����ţ�л�����ǰ�壬���Ҵ�ߺ�ȣ��������ա�����Ȼ���ⶼ�Ǻ����Ҳ��ᡣ
��������ҹ��Ұ�Сţ�����Լ����ɹŰ��������ಽ�������ں��档����Ϊ��Ҫ���ڸ���һЩ���顪����Ȼ�ǽ���������θ��õ���Сţ��׳�ɳ��ⷽ��ġ�����û��������ҹ��ʵ�Ѿ����
�����ص�������ҳ�ţ�̸�Сţ���¡�������������Ŀ��������������������һ���·������DZ�Ѱ�����ɹŰ�ȴһ�������Ҿ��ù��»�ȥ���ң�����û�ж���������Ա��Сţ����������
������ȫ������������ǣ�ҡҷ�ĵƹ��£����¾�Ȼ������Լ������ӡ�������һ�������������Ӽ���Сţ���ϣ����Ը��İ��������м��ؿ�����һ�ۡ�
����˭֪���»��ڼ����������ϵ��·���һ������������ֱ����ȫ*��
���������ϵļ����⻬��ʵ���ڵƹ����������ԣ������������Ļ������䶯��ԭʼ���ӵ����������˻�Ȼ�ص�ʷǰ�������
�������Ȼ�ؿ�������������һƬ���ҡ����������߹��������ҵ��ַ����������ϣ�������չ����ͼ����ʽ�Ļ�����Һ���Ӧ����һЦ����ƽ��������˵�����Ҳ��ǻ�Ů�ˣ���ֻ����Ҫ��һ�����ӡ�
�������˵����ǰͷ�Ի���Щ����������ô���ⷬ������һ�ױ�ˮ�����ҵ�ͷ�ϣ����������侲�����������������֣�������˵��������Ҫ���Ӹ������й�ϵ��������ʲô��ƨ��ϵ�����ֲ�������վ���������
�������º�Ȼ������ס�ң���������һ�������ҵ����ϡ�����Ϣ��˵�����æ������������ӣ������ĸ�ĸ�������ҵġ�������Т˳��Ҳ�Ǹ����ˣ�����ϲ���������Ƶ���һ���˵ļ���ϡ���
�����ҿ�Ц���ã�����æҲ��������κΰ�æ��������Ҫ������Ը�ģ������ǽ�в�ȡ����ƿ����£����������æ�Ұﲻ�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