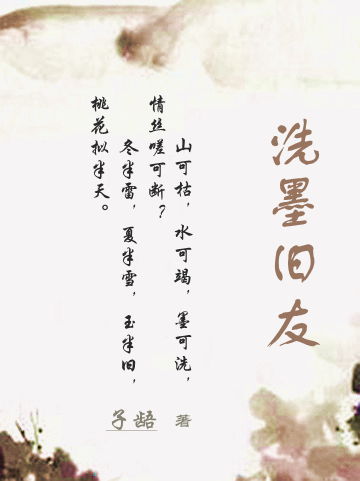洗墨旧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海川君木板板见礼:“不知今日吹的哪般好风,竟将颜老爷给吹了来?”
颜老爷?姓颜的老爷?
方才还热烈的目光立刻结冰。这丰良县方圆十里,除了大官人颜孝亭,颜司铭他爹,哪里还找得到第二个颜老爷?
哼,下梁不正定是因为上梁歪,有颜司铭这个混球儿子,上头还能是良善之辈的老子?可见颜孝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是,这颜老爷似乎保养得太好,看上去忒年轻了点……
男人含笑回礼,我凉薄看着。“先生这是要做什么?”他掸着衣袖上的雨珠,意味深长扫了眼旁边老神在在的人,转回去霭声道,“是不是犬子又犯了什么错?”
海川君道:“看眼下情景,加上书衡自白,恐怕,他二人要将考试舞弊的名头坐实了……”
“且慢——”我急忙开口,众人各色视线中,我向海川君作了个揖,“张先生,请听卞仁一句。学生并未看过这张纸条,更不曾在上面写过答案。”
海川君冷言:“老朽并未说你写过答案……”
我道:“也未写问题。不信,学生可写几个字,先生一验便知。”
颜孝亭笑盈盈插口:“听起来不错。不过,这现场写字,笔迹可随意更改,如此一来,验字岂非多此一举?”
我暗中冲他翻了个白眼。海川君蹙眉,眼色清寒:“不止是字迹问题……”
颜司铭闻言再度邪笑,我不由一阵发怵。
刚想开口,忽有人笑道:“书衡兄,子车兄,到处找你们,原来你们在这里。”
这声音……我回头,眼中一亮。门口穿着月白布袍的人挥挥手中书本,浅笑道:“你们的书忘拿了。我刚好看见,遂顺便帮你们带一带。”
颜司铭脸上陡然一寒。
大概是我的错觉,颜孝亭眼中亦似乎深沉了一些。他含笑问道:“这位公子是?”颜少爷阴阳怪气地抢答:“我们宿馆里打杂的。”
来人不语,算是默认。他的确会因为手头拮据,偶尔帮同窗跑腿做杂活。
颜孝亭的问题不了了之。一干人见完礼,来人又道:“方才听你们似乎在争论字迹问题,正巧,两位兄台的书都在此,张先生何不借此二书一验?”
对对对!这也是我想到的办法。就是不知为何,本来水到渠成的法子,经此人的口说出来,却生出股醍醐灌顶的味道。
我冲他感激一笑。他含笑回望我一眼,云淡风轻间,将书在案上摊了开来。颜司铭一张脸早化了霜打过的落木,青黄中泛着白。
两本书,两种笔迹,仅一本与纸上相同。这场救火的雨很及时,带了点雷。
那团咸菜展开来,是一幅龙阳秘戏图,图侧以行书作了注解——“秘戏图考”,恰与本次月测自选一考证题目的要求相符。而颜司铭那本书上,从扉页到最后一张纸,页页画着春宫图,姿势各异……
作者有话要说:
☆、〇八
屋子里一时安静无比。海川君铁青着脸核对过三样物事上的字迹,沉默了很久,木然道:“此事确乎是一个巴掌,尚未拍响,卞仁所言并非信口雌黄。”
颜孝亭的笑容愈发灿烂:“先生说的甚在理。只是,犬子向来顽劣,于读书一道终归欠了点火候,情急之下做了错事,坏了规矩,并非心术不正有意为之,还望先生海涵。”
“话虽如此,然《大学》有言,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意诚心正,乃为人根本,令郎亦不例外,如此心有旁鹜,岂是孔孟之道所能为?”
心有旁骛,指的该是那些春宫图了。我幸灾乐祸地有些想笑。然看到送书人那张秀雅的脸,又统统忍了回去。
“况作弊事小,却关乎礼义廉耻的根本。若是纵容一个,后面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如此一来,置信义于何地,更置国之根本于何地?吾等为人师表者,宁肯杀鸡儆猴除恶务尽,也不能养痈贻患纵虎归山!”
我看傻了眼。啧啧,真不愧是差点中了状元的人,连抓月测舞弊案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跟国家根本扯上关系。
送书来的人袖着手看,神色似也颇为欣赏。颜孝亭笑吟吟听着,还时不时点个头,以示赞意。
“秦院长三令五申,但凡于考场中舞弊者,一经查实,悉数逐出濯锦书院!”
唔,看来月测舞弊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慷慨激昂的余音中,颜孝亭淡淡地笑:“院长那边,自有在下斡旋。”
一时间,海川君失语了。此番你来我往,便在此断了。
送书人静悄悄瞅着,我干巴巴杵着。
啧,奸商见人说鬼话,见了牛头马面,又开始说起了人话。真不愧是一代儒商颜大官人,不仅做生意做的滴水不漏,就连替儿子遮丑都能把话说的这么进退有度。
海川君虽有咬不烂戳不歪吹不倒硬挺挺一根脊梁骨,颜孝亭却有煮不烂蒸不熟捶不扁华丽丽一张厚脸皮。台面上对垒,你几时见过脊梁骨打赢厚脸皮的?
老书生海川君显然不是奸商的对手,微微蹙了蹙眉:“此事……须从长计议。”
送书来的人适时冲先生拱手笑:“先生,若无他事,学生先走一步。”
海川君点头默许,那人前脚出门,我后脚立刻告退追出去。
桂雨冷浓,秋寒袭人,我拢拢衣襟小跑。绕过回廊时,那抹月白身影撞进眼帘。我朗声道:“啓均兄,请留步——”
人回转过来,无边秋雨中,我隐隐见那阡陌之上,莺啼蝶舞,柳花纷飞。
他背对雨帘,目光绰约:“是子车兄。这雨打芭蕉,落花零乱,颇有风姿,想必子车兄到此,也是为了赏玩罢?”
我怔了怔,笑道:“啓均兄,恕在下胡涂,这深秋微寒之际,不知哪里来的芭蕉花?这楼外放眼皆是一片桂树,又哪里来的芭蕉?”
花啓均笑了笑,望着雨帘道:“取其意而弃其形,意为上,形次之。”
我顿时了然,却道:“啓均兄的意思是,这雨中桂树枝叶粘连,颇有芭蕉之姿,而秋雨潇潇桂花斜飞,又像极了那雨打芭蕉之态,故谓之,雨打芭蕉落花零?”
花啓均回眸看我,嘴角噙着笑意:“子车兄,大智若愚虽好,可要是过了头,可就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我心中暗惊。他怎知道,我是故作胡涂?
作者有话要说:
☆、〇九
依稀记得,离家之前,娘亲捧着我双手,两眼潸然:“儿子,到了书院,一定不要太用功,不要想着出风头。娘对你别无所愿,只希望你平平淡淡,做一勺开不了染坊的白开水。”
我愕然:“为什么呢,娘?”谁家父母,会不盼着儿女出人头地为祖争光?
娘语重心长道:“枪打出头鸟。濯锦书院藏龙卧虎,贵胄如云,若你一进去就抢了人家名头,人家还会与你好相与?做人还是低调些的好,将来为官了,做事才好高调。”
我茅塞顿开。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开头耀武扬威的,往往都笑不到最后,比如那个在乌江边抹了脖子的楚霸王,愣是没扳倒一开始被他骑在脖子底下的刘邦。
娘真是秀外慧中,一席话切中肯綮,免去我多少无妄之灾。于是,我韬光养晦,专做一个难得胡涂的书呆子。四书五经八岁时便倒背也能如流,在这里却还不时错写漏背几段字,同窗间吟个诗作个对,我从来只缩墙角当花瓶。
我只得苦笑道:“多谢啓均兄金玉良言。在下只是……不想惹麻烦。”
这是实话。
花啓均名飞,字啓均,如我一般亲缘不厚家底不殷,在书院的前途却比我黯淡许多。他一年前刚来濯锦书院时,也曾在月测中拿过魁首,其人又难得的是一个面相清雅,其色可餐的。然树大了会招风,啓均脱颖,一时惹来妒忌无数,据说连被子都被人偷偷扔到马厩里过。
这就是他不知收敛锋芒的后果,也是书院诸位后生引以为鉴的楷模。
后来,他也学乖了,课堂上不再频频发问,同窗间盛行的诗友会也不再参加,一载荏苒,渐渐混成了众后生眼中真正的中庸。
一开始,我也是这般看他的后生中的一个。
直到近来发生的许多事。
花啓均回我一笑:“还以为此番进了修罗殿,子车兄能卸了那书呆功力。岂料险些做了李代桃僵的羔羊,呆子功夫不但没减,反倒愈发见长了。”
眼见越描越黑之势渐成,我赶紧撇清:“啓均兄,在下也是不欲变成墨缸中一缕浑水,实为无奈之举。”
啓均兄瞄我一眼,对着廊外悠悠道:“富字上面一宝盖,中间一张口,下面一方田,喻示这求富之道,无外乎三条路:一是为官作宰,二是拥田敛赋,另一条,便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子车兄口中所谓墨缸浑水,不知指的是哪一种?”
作者有话要说:
☆、一十
好毒的眼睛!我暗暗赞叹,叹口气道:“三者皆有。”
濯锦书院面上是书院,里子却是一个小朝廷,各人拉帮结派,党羽之争不在话下。如颜孝亭这般的无良奸商,丰良虽小,算起来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至于拥田敛租,压榨乡民的地主乡绅,这书院不就是他们办的?要多少有多少。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地主奸商之子又好得到哪里去?看看颜司铭就该懂。
花啓均道:“孰者为最?”我愕然,他又道:“子车兄,人生在世,什么都可能缺少,却有一样东西,从来如影随形,那便是,选择题。”
我顿悟,忖度片刻后坦言:“在下愚钝,这孰轻孰重,实在分不太清。”
啓均垂眸,须臾忽道:“在下祖上,也曾为商。商海中的尔虞我诈,并不比官场的波谲云诡少。”
我道:“因此,啓均兄家中弃商?”所以你才潦倒至此。
他转过头,淡淡扫我一眼:“小鱼总要被大鱼吃,吃再多虾米,也是徒劳。”
我怔了怔,道:“还是啓均兄看得透彻。”
啓均将手伸进雨中,缓缓道:“光阴能红了樱桃,亦能绿了芭蕉。子车兄,韶华易逝,流光抛人,有时候,人不得不为了抓住某些东西,而放弃其他。”
见他眼中幽凉,我一时怔忡,忽的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想他该是与谁家小姐两情相悦,却因门第之差而劳燕分飞,此刻悲起了秋来,遂干笑着岔开话题:“啓均兄,前日你暗中替我留门,我忘了说声,多谢。”
前天晚上到草堂点着偷偷省下的蜡烛替人抄罚书,忽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我赶紧吹灭烛火,只听窗外一人道,子车廿那个傻子,不知又掉到哪个茅坑里了,待会儿回去把门锁了,今晚就让他冻死在外面!
另一人不迭声叫好,老子一蹦三丈,冲到门口又生生住了脚。此时回去,不就等于让人知道老子在这里替人做苦力?声名本有瑕疵,多惹点尘埃倒无妨,可若是雇主请人代笔的事传到先生耳朵里,雇主被罚,老子又岂会有好果子吃?
于是,我眼睁睁看着两人勾肩搭背渐渐走远,自己留在屋里肝火腾腾,许久才一朵游魂往宿馆飘。
心底凄凉正升到一半,十步远处,房门开了。
啓均笑道:“我那时是内急才出门。解救你实为无意,你不算承我情。”
我知花啓均不是个对小恩小惠图回报的人,故未再提,只道:“方才啓均兄问我何者为最,不知你自己如何看?”
花啓均淡淡一笑,张了张嘴,眼中一丝亮光滑过,道:“舅父。”
作者有话要说:
☆、十一
我呆了一呆,半晌才反应过来花啓均不是回答我,而是真的在叫舅父。
海川君从我身后绕过来,对我点点头,便将自家外甥领走了,留我一个在那里赏玩“雨打芭蕉”。
我这才明白,每每张子涯与花啓均相遇,为何总是神色暧昧地对望许久。当初还以为,二人是皆有断袖之癖,结了分桃之好……
唉,春宫图以后要少看了。尤其是龙阳善本。
也不知发了多久的呆,江贤急匆匆赶了来。我笑道:“忆卿,何事如此慌?”
忆卿是我在濯锦书院的好友,也是唯一的台面上的朋友,颜司铭整我时他没少帮我。平日除了总爱一惊一乍,贪点小便宜,闲来无事再看点春宫图,基本没什么毛病。
此时他喘着气道:“卞,卞仁,这下闹大发了……”
我神色一凛:“出什么事了?”
江忆卿又喘了许久,才道:“是颜老爷……”
脑子里晃过颜孝亭那张奸诈的笑脸,我按着突突直跳的额头道:“颜老爷?他怎么了?”
“他……他……”
“忆卿,别急,把气理顺了再说。”
江忆卿依言深呼吸,半晌才脸色沉重地道:“颜老爷他,想请你,去洗墨斋,赴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