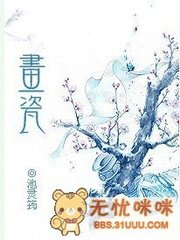求不得˙画瓷-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芳姨被关押在东向的房里,大门挂了锁链,旁边只有一个送饭的小窗。因为不想被人认出丝绦,于是也没叫侍卫来开门,她们便开着那窗户说话。
我没有回避,坦荡地站在丝绦身边,任由芳姨恶狠狠的目光将我扫了好几遍。有我在这里,她们有许多话不方便说,可我只答应丝绦带她来看芳姨,我已经做到了。
可每个人都有软肋,丝绦转过身来哀怨地看了我一会,我便低着头走开了。站在不远处的一棵苍老的树下,还可挡挡风。不过这秘苑里万籁俱寂,她们说话的声音被风吹过来,十分清晰。
“公主,你受委屈了。”
“芳姨,你们怎么被抓的?”
“狗皇帝派人抓了很多人,但凡在京城没有户籍或者没有通关文牒的人都被抓了起来,一个个审,我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一直躲着。直到除夕,想趁着守岁那会溜出城去,没想到外头有埋伏。”
“他打算把你们怎么办?”
“不知道,他很古怪……公主是不是因为我们才被要挟了?狗皇帝上次来说,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是不是真的?”
丝绦回头淡漠地望了我一眼,说:“迟早。”
“那就是还没有?公主千万不能答应啊!”
“我和他谈妥了,我给他生个孩子,他会放了父皇。”
“什么?蛮夷就是蛮夷,从来都言而无信!公主万万不能听信他,这样只会被他玩弄于鼓掌!”
“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芳姨。”
我竖起耳朵听,除了叹息,什么也听不见了。看来她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我放宽心走了过去,拉着丝绦的手说:“放心,我应承了你的事情一定兑现。只要你听话,他们在这里好吃好住,还有人伺候。”
丝绦斜目看我,苍白无力地笑了笑,“那就这样吧。”
简单几个字,令我心胸狭窄得难以容忍她任何的冷言冷语。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吧,不是你情我愿,而是胁迫。我就像个十恶不赦的人,不择手段地将她禁锢在我身边。
可是我很冤枉,明明是她先来招惹我,明明是她用我的满腔真心作为筹码。
为何到头来,我成了恶人?
明如镜…5
直到这一年开春,逃人法完全废止,放宽了服装的限制,汉人可通过儒师举荐报考科举。
我出宫巡视,能感受到平淡和麻木背后隐隐的生机。他们要活过来了,不再是被苦苦压抑的奴隶。我们祖先想要奴化汉人的愿望也终于落空。
马车行至一座桥旁,我连忙喊停。
这条河,河边的梅树,即便换上了春装我也熟悉得很。我与丝绦度过的第一个上元灯节就在这里,那时候她站在树下面等我,亭亭玉立。
丝绦也下车来了,默默站在我身旁。
我拉着她的手说:“还记得吗?在这河边,我第一次捧着你的手。”
捧着她的手呵气,用自己的掌心温暖她。回想当时的画面,心里头流淌着低缓的情意。我将她拉到自己怀里,低声说:“告诉我,那时候你对我有几分真心?”
她垂目道:“那时候你是贺睿之。”
我心急解释:“有何区别,那不过是个名字而已。你抬头看看我,哪里变过?我对你,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她眼睫一掀,定定地看着我:“那你又凭什么判断我现在对你不是真心?”
我噎住了,这种事需要理由和借口来分析判断么?我知道爱一个人不是像她这样的,不是像她这样处处算计、处处提防,不是像她这样用自己做筹码来谈条件。
苦笑了一番,转身上车。
待到那株绿油油的梅树来年开花时,她还在我身边就好。我也只有这样微薄的期盼。
听说甯太妃进宫了,大概要去慈宁宫请安。
我命人截住她,带她去佛堂见母后。
算一算,母后在佛堂也住了将近两个月,天气都转暖了,她还不愿意回宫。不如趁甯太妃进宫这机会把她劝回来,将身子好好调养一番。
不过我刚从御书房赶到佛堂去,就见甯太妃匆匆忙忙出来,说是得了太后恩准去探望察德。我也就随她去了,到底是至亲骨肉,一年才见上一面也是在情在理的。
母后住的地方很清净,院内只有几株稀疏的竹子,屋里简陋极了。
我说何必呢。母后一反常年的从容神态,卑微地跪在佛像面前念叨:“哀家也是想恕罪,希望那些报应不要报在我们的子孙身上。”
玲珑的死,对于母后来说是一场浩劫,将她彻底击垮了。我宽慰她道:“朕还年轻,将来会有很多子嗣。母后无需想太多,如今应当颐养天年。”
母后徐徐叹道:“皇上,哀家想捐银替呼延家修陵。”
自皇后被废,呼延家族已经散了。而且呼延硕的罪名很重,哪里还能让他光宗耀祖?我正想反驳,母后又说:“皇上下手还是狠了些,呼延将军毕竟是开国勋臣,他只是性情耿直,并无反义,皇上何必赶尽杀绝。”
“若不是呼延硕放肆妄为,朕哪里会赶尽杀绝?就算要治他,也必须有个名目才是。朕在做什么,天下都在看,哪里敢滥杀重臣。”
母后抬头望着我,“那呼延将军又犯了什么罪?”
“呼延……”呼延将军竟不是母后派人暗杀的?我惊愕不已,又必须极力掩饰自己的一切情绪。不是母后,那便只有一个可能了。察德遇刺,呼延遇刺,晋国公凭空消失,我大致清楚了白莲教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只是心里总有一些避讳,不愿想起那些事,那些和丝绦有关的秘密,我其实都可以装作不知道。
“算了,既然都已经发生了,那哀家也只能多给他们烧香。”母后由侍女搀起来,随我走到偏厅里去坐着,喝了杯茶,又问:“皇上,晋国公那件事打算怎么办?”
“既然说了晋国公还在宫里,那就再找个来好了,反正宫里没有人见过真正的司马缇。”
“难道一直这样拖下去?”
“再过些年,等那些旧臣都老态龙钟了就给晋国公办丧事,想必几十年过去,他们也认不出来他们的皇帝了。”
“总之,小心仔细一些,此事切不可败露。”母后平和地看着我,像很久以前她看父皇的目光,不再急躁、不再焦虑,终于觉得我是个真正的帝王了。
母后留我吃一顿斋饭,我便陪着她吃了。
几样清淡的小菜依次呈上来,令人胃口大开。
母后见我吃得很好,面容和蔼了许多,回头问侍女:“沫儿呢?传她过来罢。”
我一愣,“她在这里?”
“这些菜是她做的。”母后难得展开了笑容,“哀家想过了,作为皇帝,一生要走过许多路,比常人的路要复杂曲折得多。若是有一个你极喜欢的人陪着你一道走,或许会轻松一点。皇上愿意册封就册封她吧。”
我一时又惊又喜,丢下碗筷朝母后跪下叩头:“儿臣多谢母后体谅。”
母后扶着我,欣慰点头道:“是啊,无论怎么样,你是哀家的儿子。哪里有阿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呢?”
不一会,侍女回禀道:“回太后,沫儿姑娘已经离去了。”
母后怔了怔,“哦?这么快就走了。她不知道皇上来了吗?”
侍女答:“大概不知道吧,她说要回去伺候皇上。”
母后看着我,好似有点神思恍惚,喃喃说:“这样……那皇上用完膳就回宫去吧,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三月的阳光很柔软,不比早春的单薄。
杏花和桃花开在沟渠旁,明媚色彩遮掩了所有荫蔽的角落。
我从佛堂出来直奔御书房,召了户部和翰林学士来拟定册封的诏书。
尽管在户籍上,达奚沫儿仍然是赫连察德的侧室,但察德被囚禁在深宫,要他的印鉴来造一封休书也不是难事。
我兀自欢喜,只要一想到她即将成为我名正言顺的妃子,永远也不能离开我,所有的不畅快都暂时消退了。
不知道她拿到诏书时会是怎样的心情,最好能假装出一点欢喜来,别让我扫兴。
明如镜…6
齐安提醒我该用膳了,我从一堆折子里抬起头来,发现天色都暗了。
都已经三月了,天怎么还是这么短。我披上斗篷,从明亮的御书房走出来,一时有些适应不了外头的昏暗。当齐安扶我上了辇车,我才发现丽妃竟然在附近。她站在一行花圃面前,正对着御书房,若不是头饰反光几乎看不出来那里站了一个人。
我朝她招了招手,唤:“丽妃?你来是想见朕?”
她福了福身子,答道:“臣妾只是在御花园胡乱走着,就到这来了,便想着来给皇上请安,并无要紧的事。”
我抬手道平身,“那你早些回去用膳,明日、朕明日去瞧你。”
“谢皇上,恭送皇上。”
因为她一直低着头,我没看见她的目光,但多少有点歉疚之意。自从丝绦住进了德阳宫,我有很长时间没去看她了。
檀木香炉里的锥香已经烧尽了,内殿里没有人伺候。
层层轻纱帘幕后,烛光映着一个孤寂的身影。
我半挑开一层,往里走了几步,“丝绦,你在里面吗?”
没有回应,我便继续朝里走。
宽大而耀眼的龙床上,丝绦着了一身绣满青花的汉服,侧头望着我。仿佛一只精致的青花瓷瓶,傲然、无暇。
我问:“怎么一个伺候的宫女也没有?”
丝绦张口,声音突兀而粗糙:“我叫她们都出去了。”
她的神情过于平静,我感到不安,走近她问:“怎么?不想用膳?”
她柔韧的双臂环住了我的腰,将脸贴在我胸膛,问:“我父皇在哪里?”
我怔了怔,“不是说好了么?等你给我生个孩子,我就告诉你。”
她的手臂环得我更紧了,“赫连睿德,你不该骗我。”
我想挣脱她,可是突然感到有尖锐而冷硬的东西顶在后腰上。一瞬间像从春天回到了寒冬,肆虐的北风吹跑了我脑子里所有温柔的设想。剥离开那些琴瑟和弦的表象,其实我和她之间横着一把双刃剑。
若生,就相互煎熬。若死,就共赴黄泉。
我伸手抱住她的头,苦笑着说:“你在佛堂里偷听了我和母后谈话。”
“我父皇在哪里?”她仍然问这句话。
我猜她不想杀我,她拿着刀子无非是威胁我说出真相。可真相并不是什么好物,我便时常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将她当作普通的女子来爱。她却做不到我这样。
我的心如那焚尽的锥香,化作冷冷的一撮灰,风吹即散。既然到了这地步,那就痛快一些好了,不是常有人说,长痛不如短痛。
我摸着她的脸,低头看着她说:“死了。”
她的睫毛静静盖在下眼睑上,问:“葬在哪里?”
“宫里死了很多人,堆在一起烧了,没有安葬。”
“我的哥哥们……”
“我们打进宫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死了,只有长兴活着。”
“姐姐说她醒来的时候父皇还活着,你撒谎。”
我无奈地苦笑了两声,说:“是啊,他是被摄政王杀死的。你就想听到这个对吗?你想听到最惨烈的真相,才好用尽你的所有力气来恨我。既然要恨,那就痛痛快快地恨,我背负了多少罪孽、多少仇恨,也不惧再多一点。你恨我吧,长安。”
她的胳膊如水蛇一样缠得我喘不过气来。她浑身发颤,却用力克制着暴怒的情绪,压着嗓音一字一句说:“蛮夷,我竟然信你,真傻。”
听到蛮夷这个称呼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一直在摆脱,以为天下太平之后,仇恨会慢慢地淡去,也不会再有人叫我们蛮夷了。可这两个字出自她口,真是令人心如刀绞呵。
我朝身侧伸手钳住她握刀的手腕,说:“我已经下令册封你为淑妃,赐章阳宫。”
她猛地用上了力,刀尖狠狠地扎在我腰上,“你以为我会当你的妃子?”
“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到死都是。”我反手拧住她的手腕,刀子应声落地。接着拦腰抱起她,撂在明黄刺目的龙床上。
她终于失控了,疯了一般挣扎起来扑向我,从发髻上拔下一根簪子想要刺我。
我一翻身,轻易制住她,笑问:“要和我同归于尽么?”
她眼里布满了红血丝,声音哑到了极点,像是全身心的痛苦都溢了出来,“若你下地狱,我就上西天,若你上西天,我就下地狱。就算死,我也不想再遇见你!”
我压在她身上,用双膝箍住她的腿,一只手便钳紧了她的一双手腕,一面空出一只手来从枕下摸出一只精巧的药瓶,一面贴近她耳畔低语:“忘了么?你母后要你活着,长兴要你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