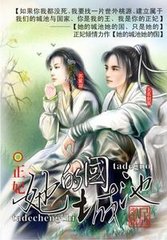���� ����-��1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ž�����������ִ�ϸ�̫�ࣿ��
���꣬��С���㡣��
����ʲô����û���ˡ�������˵������������ǰ�ո����������˳�ͻ���������Ϊ�Ǿ��ùá���������˵�Լ�λ�ݸߣ�ӲҪ������������֪��ô��������������˵�˾䡮�����û����Ҵ������٣������ɵ��ٸ�Ҳ�����˷�ˡ�����������һ�ع��������������ڿ�˵����ҰѾͷ�����������������桯�����ǰ����С̫��Ҳ��������
�����⣬���ⲻ�ɵ���Ц������������һ�ף�����һ�ף��������������Ѳ����ʡ���Ů��ö������洫���ڹ����������˰���������Ϸ�Ĺ���ȴ����Ƿȱ�����������ᣬ�������Ѱ��ͽ��꣬�������¶��������������������Լ�������δ����������˵��ʱ������˸����˵�����鴦���Dz����������Ȱ����棬������������ڸǣ����DZ���Ŀ������Ļ���
���˻��������ͣ�ˣ����������������ʻ���Ů�ٹ��ɴ�һ���춯��������������һ�ˣ����˶��������˼��±�ͣס�ˡ�
����پ����ԣ���������λ���ƺ����ǰ����Ϸ�����
�����������������ˡ�
���˹���·���Ե�������ֻ������ɸ�����ɳ�ӣ��ߵ�ɢ�飬ȫ���ĹǼܶ��������䲻��һ�塣ͷҲԽ��Խʹ��Խ��Խ�Σ��л���Ҳ��֪���˶�ã���������ͣ�ˣ�ֻ������Ů��˵�˼�������˳��������ڸ��ϵ����ƺ����������ļ���
�������←��һ�������Ǵ���һֱ����������������������ǵ���Ů�ٷ��أ�����δ�л����ȥ����Ҫ�ʹ˻ع��������ߣ����ѱ��ƵĴ�����������֫������������������˹����˷���Ҳ���������ˡ�
�������ĻŽ��ǣ�˼���Բ�ʱ��ͻȻһ��ǿ�����˽������������ˡ�
ǿ���Ŀ������ѣ�ж�����ij�ֱ���̽�Ӵ����ľִ��������ʣ�ֻ���н����ۣ�����Ҫ����϶������ˡ�����ɫ��������ɫ��ѥ��ϸ����ף�����Ѫ��Ĵ�����������Ŀ��������������⣬���Ƿ��̡�
��ū�ŷ���С�����������������Ƽ�ϸ�����˷��飬��������ɨȥ����ק����������������һʱ���ֽŽ�Ӳ����ֱ���ܣ�ֻ����������
���������ùã���
����Ů�ٲ�֪�ιʾ���˿췵�أ�һ��������ˡ�
���̱����ų��ţ������Ʋ������ɷ���ȴ�����۵�һ��������ɱ�⾪ס�����������⣬������Щɥ���ڴ������£���ɱ��Ҳ���������������
�ͼ�����ת����һ�Ѿ�ס���ˣ����в�֪��ʱ���˰Ѽ�����ৡ�������һʩ��һ��Ѫ�����ּ��졣
˲��Ѫ�����䣬�Ƕ�Ů��ֻ�Ŵ��˲������ŵ��ۣ����������ȶ������������־嶼δ�����֣�����ֻͣ���ھ��ȵ���һ˲������Ѥ�õĻ����
�̽��������������һ������˻˻��Ѫ�Ľ�������������ȴ�����ɲ���
��Щ���Ƿ����һ��������
���ɫ��Ѫ�罦�������ϡ����ϣ��������ȣ�������ʬ�������Ӷ�����۳ɹ�����ұ��ͼ����Ⱦ��һ����������ǵ�ɢ����ζ��
����������һ��֮�
�������ڲ������dzЦ���������ֶ�꣬������ȥ��
���Dzٵ��ķ��������������������ۣ���������һ����Į�ķ���ʱ�������죬������˵�˾䣺���ߡ���
���ų����������𣬻���ǰ�������ŵ��¶��ڳ��ڶ�����˵���������ڣ�һ���Թ��Եò���ذ�ף�һ����Ů�����Ϸ�������ϸϸ�������ա�
�������գ�˲Ϣ�������ڣ�������ɭ������������Ϣ������ֱֱ�������Dz���������ð����Ѫ�����ƺ�û��ͣ������˼��������ӿ��ȸԾ���������Ӳ�֪��һ���˿�������ô��Ѫ�����ɫ�����ɫ���ɫ����ɫ���������ָ��ӵĺ�����һ�𣬳�����һ���˵������������������գ���������ΪѤ������Ⱦ���ʻ������ԴԴ������������
ֻƬ�̣���������ü�����˿ڱǣ�ͻȻ˵������������ٲ����������Ǻܿ�ͻ��������档��
������ʵ��ˣ���δ�뵽������һ�У���Ů�������������֣��������������ܣ�ֻ���䵭�������������Ӹ�������̬�����ݲ��ð��ɳ�ӣ�����������ü�����ĵ��Ƕ�������Ϊ�˲���������עĿ������ܲ���Ѫ����ζ��
�գ�����ĬĬ���������ֳ���
����������æµ��������쳣ɳ�ƣ������϶���ô�������ô����
�����Ц�Ļ��ӣ��۵�������˼��������ڵĻ�����ҭ�ˣ������ѹ���ɱ��ɱ��˳�֣��������Ѹ�٣�˵���Ļ�����ô��Ȥ��Ц��Ī���빬ǰ�����������������£�����˵��ģ���
���Ǻǡ�������Ц�ˣ�Ц�����䣺����С��Ͳ���Ҳ���ҡ��������������ݺ�һ�ȣ�������䱩��Ĺ⣬ɱ��һ��������
����һ���Ҳ����Ǿ��ùá��ڶ���������������Ҳ�����˷����ʵ���������һ�̡�����������Ҫ���������أ��ֺ���ɱ�������ˡ��������������˵�ս���̧����ڶ��棬�����۲һ�Բ������
���̣��빬ǰ������ţ��������Ǹ����ȴ��֪�ι����˹���Ϊū������ʹ���������ʷ�����֪�ڴˣ���Ȼ�ɵ�����ȴ����Ȥ̽����������Ҳ������һ����ÿ��������һ������Ϊ��֪���£��еĿɼ��⣬�еij�ª������
���ܾ�����ҡҡ�λε������ã�ֱ���߸��Ķ�������������֪���ⶨ������ɽ·��
б������ʱ�������������������������������ۣ���������������а�����У�����˵������ʱʱ�̿̾����ţ��ڴ������������ϴ���������ʵ�뷨��
ֻ��ϧ̫���չ���̫�࣬���㲻�����ˣ���δ�ؼ��ö�Ů�ˡ�
����Ц��ȥ�����������۵ļ�����Ū��������ô����
����һ㶣��漴�����ۣ����Ҳ��Ǹ����ˡ���
���ۣ�������Ц���������⻰����һ�������ˡ�����ʵ�ڿ�Ц������Ů�����ʵģ����Ӵ��ֻ���������裬�����쳣����������䵭ƽ���ij���������ͷһ�⡣
���Ƿѹ��������ڿ�ʲô����Ȼ�������˺ιʶ���Ů�ˡ�����˵�գ��������������Ƕ�����ۣ����м�ŭ������ζ��
���̲�δ�ӻ���ֻ���ţ����³�����
����üdzЦ�����´�������̬���ݵ����˳���
̧��һ����һƬ�տ���
һ�����ݣ��������̣�һ����ͩ����ʯ�����ʣ�ԶĿŨ���ػ����ģ�������������ڵ�����������������ˮ���������泩�������ɽ��ˮ���ľ���
�Ų�����������СԺ��ƫ����С���峺������ˮ������ת�������Ż��㡢ҩ�㣬����ˮ����ˬϮ�ˡ�
ǡ�ڴ�ʱ���ſ���һ�����߳���
���������������Ц����Ť�����ѣ���������ɳ���ѱ���ۣ���������С�㡣��
�������������������Ź��ȣ�������ֿ�������ķ��̣�ŭĿ���ˣ�������ȥ�ɻ����˵�ţ����������أ�����ʮ�㡣������������dz��������Ŀ����ȴ�������ϣ�һ���ֲ��¹�ȴ�ɾ����࣬��˿�����ޣ��������ڹ�������IJŻ���˾�Ȼ����
���̶�����˵���������ӿ����˸�����������ȥ�����ⲻ����������������⺢�Ӳ����£�����С�����鷳�ˡ���
���ⲻ�˳������ֱָ�����ڡ�
һƬ����谵��˿˿��������Ƣ�����������˸���������䣬�þ��������硣����ɨ��һȦ��Խ��Խ���澿��������˭������˺����飬�����£���Ʒζ�������ܡ�
����Ҳ�ǹ�������ģ����������ǻ�С�ӵ����
�ڶ���
����Ҳ�ǹ�������ģ����������ǻ�С�ӵ��������˵�IJ������죬���ⲻ��һ��������ȥ��ֻ���Ǵ�Ƥ���������ѳ�һ��Ц��������Ծ�����ӳ���ţ���Ӱ�߰ߣ������������֡�
���ⲻ��µ�����Ȼ�����˴����⸾����̹Ȼ���䣬���ֺα��ʡ�
����С���������ɷ����ϸ�˵��һ�ι��£����������ʻ�����������ǿӲ������ռ����������
���������鼸�ԣ���������һ��������һ�����������粦�Ƽ��հ�����չ��������һ�뱻һ���鵲ס�������Ƽ�����Ů������꣬�����̬������ٱ���Σ�����ס�������·��ģ����ǹ�͢ɴȹ���䣬�Խ�������˿�У�����ȹβ��������ӯӯ������һ�ء�
�ӻ�����װ�����ʿɿ�����Ӧ�Ǿ���������λ�ߣ��ּ��²�һ��Сʫ������ˮ��������ʩ�B��裬�@�۷��������I�ҽң�������������ʿ�ЖA������ӡ�´����С��Ѿ�ȫ�桱�ĸ�С�֡�
��������ʮ���ꡭ���������������������������ȵ���λʱ�����ˣ������˺ϸ�Ҳ���ȵ۳���������Ѿ�ȫ��������δ�š�
���ϸ������������䣬�⻭��Ů�������ҡ���ɳ�������Ʋ�˺�ѵ������ڶ��ϣ�������Ȼһ����������ʮ���������ڲ�����ʮ���꣬����Ů�Ӳ���˫ʮ�껪��������ȴ�������꣬ʵ�ڲ���֮�ˡ�
�����⻭���˾��Ƿ���֮������
�˻����Ǻ������ţ���Ϊ��������뻭ʦ˹ͨ��������������ܻ���
�������Ƭ�̣��Ѹе����´�����ͷ��ֻ�����Ỻ��������͢��ʦѡ�β��������ѭ����Ҫ�ȹ���㿼�أ��ڹ��������빬�����죬ѧ�������������ǣ�ֱ������֪���ˡ��طִ緽�ɣ���Ϊ��������ʱ�����˼ල���Է�����֮�¡�����������������γ��£���
��������Ц�ˣ��渵�����
�����Ա�����ʮ����ǰѡ��ʦ���˷�����أ������Ľ���ѡ��������Ϊһ���˵Ĺ��������Ѿ�ȫ�������귽ʮ�ģ�ȴ�ѲŻ����ڣ��������ʣ��������ɣ���֪���������ر��ֶ���ø���ϲ�����������и�������������ȷ��������ˡ���Ȼ��������Ե��ѣ�������ò�����߲�����֮��ֻ��ϧ����һ�Ų�¶���档
��ʱ�ȵ��ѹ�������谮�Ĺ�������֪��ʶī������ϲ���������ȵ�Ϊ�ֻ�������Ѿ�ȫ�������ڡ����䱾�����ٻ�֮�ң���С�㰮����Ū�£���֪�ȵۺ��䲻��С�������꽥����������̸����Ͷ������ʱ�Ѿ�ȫͻȻ���֣�������̸��ֹ���������ʶ��������������������ҷѾ�ȫ�������ڣ���ʫ�ܵ������ü������ġ�
���Ͳ�ס������Ѿ�ȫ��������IJ���������������������ꡣ���ǣ����»����Գ�����������Խ���׳���
�ɡ���ǽ�ж����������ˡ����Ͳ�ϡ�棬����˵���û��ñ㱻�Ҵ���
���˲�մ�£��²����ˣ����ܱ������������š��ϸ�����մ�ˣ���մ�����մ�ġ����������ȵ����Ͷ��ƣ���˵����ҿ��ϴ������ֶ��ʹ��ˣ�������һ����������������ɳ�ƵIJ���ϸ��֮�µ��ż������ʿ�ǻ��
���ⲻ�ӻ������з�����֪�������������������������ƺ�Ҳ��˵�ȵ���λʱ����������λ����������������Ҳ������֮һ��
���������棬����̾Ϣ��
������ң����������ڹѣ�Ҳ��������֮�ˣ����������Ը��ң���Ը������Ҳ��Ը������������֪�ǷѾ�ȫ��ʱ���ڣ��ڿ�����˵�����ٲ����£����������գ������ȵ�����һ����һ��֮�������dz��������ڵز������ţ������ȵ۳�Ц���������������������ˣ��ø�����Ӣ�����ø�̰���������������ȵ����������Ƿ��ڣ�����ֻ�𣺡����鲻�ڣ�����ȴ���䡣��
���������ȵ����˶������ң����º�����ò���٣���Ҳ��Dz���˹���û���վ���������ް�ŵ���Ϣ�����ǷѾ�ȫ���䲻��������������Ϊ�����¶��ơ��������⺢�����±�����������ˡ�����������̫��ı��ǰ;��������仹��������ô����
�⻰һ�������ⲻ��������Ц���������������Ľ�̸��ʵ��˵һ�룬��һ�룬��һ�룬Цһ�룬�����������ȴóȻ��İ����̻¶���飬��Ȼ�й�����֪����Ȩ���Լ��������Լ�����Ů�ӵ��鰮���մȾѪ�ȣ����ս��ɱ����Ϊ���������ӳ������ӳ����ó裬ʧ�������ͬ������Ҫ˵����ϻ���������������ŵ���һ�仰��
�������ڿ���������̾Ϣ����Ȼ�˽�ǵ������������������¹�������һ�������±�����ͼ����һ˵���������̱��·���֣��漴�����˴��������Գ�����֮�ˣ��Է��������Ի�����̽������������ͼı��
��Ȼ�����ⲽ������������Ҳ������֪������������
˼���ˣ������Ŀ��������ҡҡҷҷ�����λε�����������������ϸϸ������������������ֻ��������һ��С���롣�����δ�Ǵ����Ƿ��̾���Ҳ��һ���롭